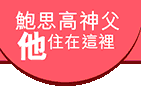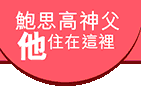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
那是一座鉅大及華麗的巴羅克建築物,始建於1644年,1673年才完工,1681年被祝聖的機構。內部由Ticino的Antonio Bettino建築師設計(他於17世紀下半葉在都靈工作),而面臨Vittorio Emanuele大街的牆身,是由Mario Ludovico Quarini (1736-1800)日後所設計及建造。
右面第一個祭台上,掛著由Claudio Francesco Beaumont (1694-1766)繪畫的一幅「聖方濟各沙雷氏在童貞與嬰孩面前祈禱」的畫像;因為這裡與一個以這位主教相關的善會,他們於18及19世紀次間,就在這座教堂內聚會祈禱。這幅畫像今天擺放在主教座堂的祭衣所裡。第二個祭台是敬獻給聖斐理伯內利(Philip Neri),由米蘭籍的Stefano Maria Legnani 又稱為Legnanino (1660-1715)所繪畫的油畫所裝飾。主祭台有一幅華麗的無原罪聖母的畫像,由Daniel Seyter (1649-1705)繪製,亦是這座教堂所命名的。
當包萊神父將鮑思高神父介紹給柏老祿侯爵夫人時,她立刻計算這位年輕司鐸將會獲得怎麼樣的條件和薪酬。在接納作為這小醫院的神師工作時,不單容許那些青少年都來探訪他,並教給他們要理,同時也讓這個慶禮院在仍未竣工的小醫院裡聚集。
在1844年10月20日前數天,鮑思高神父將他的住所遷往濟良所去。他的房間就在濟良所門廊上的第一個房間,旁邊有包萊神父和Sebastiano Pacchiotti (1806-1884),他是柏老祿夫人事業的另一位神師,他日後也協助教導青年中心的青少年。「神學博士包萊說:『那間為你用的房間,可以暫時把它利用,以聚集那些到聖五傷方濟堂去的兒童。到了我們可以搬到在小醫院旁,那所專為神父們預備的房屋裡去的時候,我們再想法找一個更好的場所。』」(《母院史》128)
於是,就在10月20日主日那天,將青年中心遷往濟良所去。鮑思高神父在《母院史》裡曾這樣記載道:
|
|
 「中午後不久,就有一群不同年齡和身份的孩子們,跑到了華道角,去找新的慶禮院。 「中午後不久,就有一群不同年齡和身份的孩子們,跑到了華道角,去找新的慶禮院。『慶禮院在哪裡?鮑思高神父在哪裡?』他們到處這樣問。
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在那裡附近,誰也沒有聽說過鮑思高神父或慶禮院。詢問的以為自己被人嘲笑,便拉高了嗓音,提出無理的要求。對方則以為自己受到了侮辱,報以恐嚇和毒打。正當情勢開始緊張起來的時候,我和神學博士包萊,聽到了吵鬧的人聲,便從屋子裡出去。我們一出現,一切的嘈聲,一切的爭吵,都立即停止。孩子們成群的向我們奔來,急急地問,慶禮院在什麼地方。
我就對他們說,真的慶禮院還沒有落成,叫他們暫且到我的房間裡來。由於我的房間面積寬廣,大可以供我們應用。的確,那個主日,一切都進行得相當好。但是到了下一個主日,除了以前的那些孩子們之外,又加上了鄰近各地的兒童。實在不知道往哪裡安置他們。房間、走廊、樓梯,到處都擠滿了孩子。
到了諸聖節日那一天,我與神學博士包萊聽告解。大家都想辦告解。怎麼辦?我們只是兩個聽告司鐸,兒童卻有兩百人以上。一個點火,一個卻想法把它熄滅。這個拿木柴,那個提水。水桶、彈簧、小鏟、水壺、面盆、椅子、皮鞋、書籍,以及所有其他的東西,都被弄得雜亂無章,其實他們是想把東西整理好的。
親愛的包萊神父便說:『不可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設法尋找一個更適合的地方。』
然而在那個狹隘的地方,即在濟良所大門內,門廊上面那個房間,過了六個慶節。」(《母院史》131-132)
|
事實上,他們在整個十一月都待在這樣的環境裡:早上,孩子們在聖五傷方濟堂參與彌撒,下午就在鮑思高神父的房間內聚集,學習要理,辦告解和其它可以舉行的活動。
假若要延續這樣的活動,是需要更大的空間的。鮑思高神父曾向法蘭騷尼總主教討論這問題,總主教詢問,這些孩子不能到自己的本堂裡去嗎?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回答說:「他們大多數是從外地來的,在都靈只過一年之中的一部份時間。他們連自己隸屬於哪一個堂區也不知道。他們中間有委多人衣服襤褸,講的是不容易懂的方言;因此,他們聽不懂別人,別人也聽不懂他們。再者,有些孩子年齡已相當大,不敢去跟年幼的小孩同班上課。」總主教便決定,「必須有一個專為他們適用的地方。」他批准、鼓勵及祝福了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的建議。這樣的承諾是要維持下去的。
柏老祿侯爵夫人明瞭這事情的緊迫,在濟良所旁仍在興建中的小醫院裡,將其中兩間大房間暫時改為小堂。(參:《母院史》13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