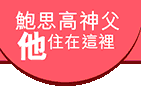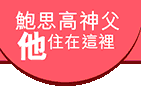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
離濟良所不遠的地方,就是細小的聖伯多祿縲絏堂墓園,是建築師Francesco Dellala di Beinasco (1731-1803)於1777年所建的。這墓園呈四方形,內裡三邊都是迴廊,另一面設有小堂,在入口處前面,一如現今,有一個廣場。為了環境衛生的理由,它位於城市的外圍,自1829年起已經不再埋葬亡者;直到1860-1870年間,仍繼續有家族式的將亡者葬於該處。這墓園是由市政府所管轄,但委派一名神父在小堂內負責宗教禮儀和為當區數個家庭服務。
作為青年中心聚會的地方,有這樣的安排:在小堂舉行宗教禮儀和要理教授;在寬敞的廣場適合為青年作遊戲之用。在得到市政府的口頭答允和小堂主任戴西奧(Tesio)神父的批准後,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於1845年5月25日(主日)開始,便將那裡聚集青年中心的青年們。
|
|
 「我們一提出請求,並有總主教的推介,就獲得准許,可以在聖十字架紀念堂,即通常所謂聖伯多祿縲絏堂的空地上和聖堂內集合。…… 「我們一提出請求,並有總主教的推介,就獲得准許,可以在聖十字架紀念堂,即通常所謂聖伯多祿縲絏堂的空地上和聖堂內集合。…… 這裡有長長的走廊,廣大的空地,又有適宜於舉行聖禮的聖堂。這一切都激起了青年們的興趣,使他們個個欣喜若狂。 這裡有長長的走廊,廣大的空地,又有適宜於舉行聖禮的聖堂。這一切都激起了青年們的興趣,使他們個個欣喜若狂。但是,在那裡有一個可怕的敵人,是我們所沒有想到的。這不是一個已亡者:那裡有許多死人,都安息在附近的墳墓裡;卻是一個生人,即主任司鐸的女傭。她一聽到了孩子們的唱歌聲、笑語聲,以及喧嘩聲,立刻怒氣沖沖的走出屋外,歪戴著帽子,雙手往腰眼裡一撐,開始破口大罵那群正在盡情遊戲的孩子。同她一起痛罵的,還有一個小女孩、一隻狗、一隻貓、和所有的母雞,好像一場歐洲大戰,馬上就要爆發似的。我想到好面前去安靜她,勸導她,說明那些孩子只是遊戲,並沒有什麼壞主意,也不犯什麼罪。這時她就對著我大發雌威,叫我快滾。
當時我認為必須停止遊戲,便給孩子們講了一些要理,又在聖堂裡唸了玫瑰經,就動身離開那個地方,希望下一個主日能更平靜。事實卻完全相反。
到了傍晚時分,主任司鐸回來了。那個女傭就對他說了一大套,把鮑思高神父和他的那些孩子都說成革命分子,聖地的褻瀆者,都是一些歹徒流氓,又催促那個老好的主人,投書市政府,提出抗議。他依照那個女傭所說的話,寫了那份控告書,而且寫得那麼嚴重,竟使市政府立刻下令,警告我們之中誰敢再到聖伯多祿於縲絏堂去的話,馬上加以逮捕。
說起來也真令人痛心,那封竟是戴西奧神父所寫的最後一封信;原來他在星期一那天,寫完了那封信之後,只過了幾個鐘頭,心臟病突發,差不多就當場一命嗚呼了。其後只不過兩天,那個女傭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母院史》138-140)
|
雷蒙恩神父(Leymone) 錯誤解釋他從公眾檔案室裡找到的文件,按他的說法,那消息是在四旬期內,之前在墳園小堂內曾主辦了多次要理講授班。
按目前最新的研究,讓我們看清當時的發展情況(參:RSS 5[1986] 199-220)。
事實上,曾在聖伯多祿縲絏堂裡舉辦了多次要理講授班,但並非那與santa Pelagia協會在其他青年中心的有關;這些聚會在五月開始,而非在四旬期內。而「審計署」(Ragioneria)在5月23日曾因不明確的理由發出在那裡聚會的禁令。但那禁令在25日那天仍未知會,故此,鮑思高神父和他的青年們仍在墳園聚會。相反,在接著來的主日,那禁令張貼在墳園入口的大門上,而市政府命令警察去執行禁令。鮑思高神父並未得悉事態的發展,心想這可能是因為他的青年們在上主日的事件所引發出來的。
戴西奧神父確實未能清楚解釋,因為按文件記載:他於28日(星期三)去世。而他的女傭 – Margherita Sussolino – 留在那裡數天,整理她主人遺留下來的東西;之後,再沒有她的音訊,很有可能是在她的家鄉去世的。
當小堂主任去世後,從文件中看到,包萊神父、Pacchiotti神父和鮑思高神父立刻聯名申請成為那空置出來的小堂主任的職務,但他們的申請卻被拒絕,而委任了另一位(6月18日)。在該月底,三位再次聯署要求在聖伯多祿縲絏堂內聚集青年們,但這要求也被拒絕(7月3日)。
在面對這樣嚴峻的情況,要為青年中心找到一個安置的場所,他們在7月4及9日,重新再次申請:能否每個主日,使用磨房(Mulini Dora)的小堂數小時。這次卻得到了准許(7月10日)。
直至該天,每主日的聚會繼續在小醫院附近相聚,和城郊的小堂聚會,它們計有:Sassi, Madonna del Pilone, Madonna di Campagna, Monte dei Cappuccini e Super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