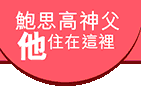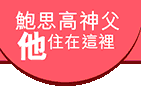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
在這僅有的兩個月時間裡,包萊神父和鮑思高神父立刻四出尋找合適的新地方;然而,聖瑪爾定堂為教授要理時卻不夠地方使用,同時,他們設想為年幼的童工開辦夜校和主日班;因此,極需要一個合適的和有供暖的地方。
在華道角區裡,即今天在進教之佑廣場的小堂,若翰.安多尼.莫雷達神父(Giovanni Battista Antonio Moretta)擁有一座兩層高的住宅,部份作為出租之用。他十分樂意將其中三個房間,於1845年11月租給自己的兄弟。
莫雷達小屋有一座地窟和馬廄,樓下及二樓,各層有九個房間,而上面有一個大的陽台。
|
|
 「那時已是11月(1845年);這樣的時節,不再適宜到城外去旅行或遠足。於是徵求了神學博士包萊的同意,在莫雷達的房屋內,租賃了三個房間。這些房屋,就在如今聖母進教之佑大堂附近,……我們在那裡渡過了四個月。雖然地方狹小,內心卻很滿足;因為至少可以在那些房間裡,收容我們的學生,教導他們,尤其是使他們能有辦告解的方便。此外,就在那個冬天裡,我們開辦了夜校。這是第一次在我們這裡,談論這類的學校。為此,到處議論紛紛,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母院史》141) 「那時已是11月(1845年);這樣的時節,不再適宜到城外去旅行或遠足。於是徵求了神學博士包萊的同意,在莫雷達的房屋內,租賃了三個房間。這些房屋,就在如今聖母進教之佑大堂附近,……我們在那裡渡過了四個月。雖然地方狹小,內心卻很滿足;因為至少可以在那些房間裡,收容我們的學生,教導他們,尤其是使他們能有辦告解的方便。此外,就在那個冬天裡,我們開辦了夜校。這是第一次在我們這裡,談論這類的學校。為此,到處議論紛紛,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母院史》141) |
夜校是從在濟良所開始的主日學發展出來的;而在翌年以有規劃的方式繼續,特別當青年中心最後找到了較穩定的地方後。就在莫雷達的三個房間裡,變成了一個容納約二百名學生的學校,十分擁擠。
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得到了神學博士Chiaves、神學博士Carpano和Musso神父的幫忙,教導這些學生;除此以外,鮑思高神父也得到了一批來自城市的年輕學生們的幫助。鮑思高神父這樣寫道:「這些小教員,起初只有八個十個,後來他們的人數不斷地增加。這種讀書的學生,就是這樣開始的。」(《母院史》190)另外,也有一些成年的志願者來幫忙,他們都是一些工匠和城市裡的小商人,我們可以視他們是首批的「合作者」(協進會員)。
主日學及日後發展成為夜校所採用的教學方法。
|
|
 「起初只教一門科目。譬如說,在一個或兩個主日上,學讀和溫習字母和拼音,然後立即以要理問答作為誦讀和拼音的課本。到了第二個主日,重複同樣的教材,加上幾條新的問題和答案。這樣,經過八個慶節日子,我能使有些孩子把幾頁的要理問答讀得出來,而且也會自己去學習。」(《母院史》189) 「起初只教一門科目。譬如說,在一個或兩個主日上,學讀和溫習字母和拼音,然後立即以要理問答作為誦讀和拼音的課本。到了第二個主日,重複同樣的教材,加上幾條新的問題和答案。這樣,經過八個慶節日子,我能使有些孩子把幾頁的要理問答讀得出來,而且也會自己去學習。」(《母院史》189) |
而成績卻是積極的:「這樣的夜校,可以產生兩種良好的效果:鼓勵青少年們來學識字;這是他們自己也感到非常需要的事。同時夜校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青少年們認識信德道理;這原是我們費神工作的首要目的。」(《母院史》190)
青年中心內的活動所得到的這些令人安慰的發展,卻引來了一系列的控告和誤解:「有人叫鮑思高神父是一個革命份子,有人則說他是一個瘋子或異端者。他們所作的推論是這樣的:『這種慶禮院使兒童們離開自己的堂區,因而使本堂司鐸眼看著自己的聖堂空無一人,而且也不能再認識那些兒童;可是,關於他們,他要向天主交代的。所以,鮑思高神父應該把那些兒童,送往他們自己原來的堂區,不應該再把他們聚集在別的地方。』」(《母院史》141-142)最後一項的指控,明顯是來自城市裡的本堂司鐸:要讓他們知道,這些到青年中心來的青少年,都是「季節性」移民,並不能夠溶入任何堂區的架構內;當本堂司鐸明白原委後,他們鼓勵鮑思高神父繼續他的工作。但其他的流言蜚語和誤解卻仍然繼續。
他們留在莫雷達的三間房子裡約四個月,最後,在二月底,莫雷達神父因為其他租客的投訴,被迫中斷了他們的合約。
數年後(1848年3月9日),鮑思高神父從拍賣中買下了莫雷達的房子和附近的空地,設想將青年中心的部份搬往那裡,特別即剛開始的「住宿」。他後來因為房屋結構十分差,被迫放棄這個想法,最後將它賣出(1849年春天)。於1875年,再次買下破舊的莫雷達房子和附近的空地,翌年,建立首個「女孩子青年中心」,交由母佑會修女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