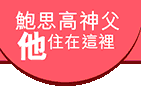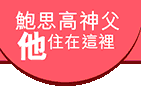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
租賃給青年中心使用的棚子是新建的。事實上,當方濟.畢納地於1845年7月14日從斐利比三兄弟(若望、安多尼和嘉祿)手中,以1萬4千里拉購置這塊土地時,那座房子仍未建成。那是在當年11月才建造的,希望把它用為倉庫或手工業的作坊。
所以,在六個月後,當包萊神父以鮑思高神父的名義簽定這份合約時,很有可能那座房子仍未被人使用過。
四周環境
在畢納地對於那棚屋做了相應的改善工作後,那棚屋便分成三部份:小堂,實際上是一間長方型的大房間,長約十五米;另外兩個房間分別作為祭衣所和儲藏室(參看附圖)。
當從西面走進小堂時,要跨下兩級樓梯,因此,鮑思高神父寫道:「所以到了冬天,或是每逢下雨的日子,地面上都是積水;可是,在夏天,我們差不多要被過度悶熱的臭氣所窒息。」(《母院史》230-231)房間面向操場那面有七個窗戶,當時,與畢納地的房子並沒有通道穿過的。在那破舊的祭台後面,有一道活門通向祭衣所。
承托著屋頂的橫樑向下傾斜,上面蓋上木製的天花板;因此,屋頂的高度剛超過兩米。在這樣的環境下,位於小堂中央,靠向北面的細小講道臺,只可容許矮小的包萊和鮑思高神父走上去。所以,在1847年6月29日,法蘭騷尼總主教首次到訪青年中心,在小堂裡施放堅振時,所戴的禮冠撞上天花板。(參《母院史》203-204)
慢慢地,鮑思高神父用簡陋和很小的東西將小堂裝飾起來,但卻能夠反映出當時的靈修觀,及日後成為青年中心傳統的敬禮。
木製的祭台原屬於小醫院的首間小堂的,擺放在東面。在那上面,擺放了從濟良所那裡搬來的聖方濟.沙雷氏的畫像。這位神聖的主教繼續成為青年中心和小堂的主保。
在進門的右面壁龕,擺放了聖磊斯.公撒格的小塑像,為向青年中心的青年們推介,和對這位青年主保的敬禮,鮑思高神父推介了六個主日的準備和九日敬禮,及將禱文印製在小冊子上。於1847年5月21日,成立聖磊斯善會(該善會規章於4月得到法蘭騷尼總主教的批准),讓品行出眾的青年參加。自1847年秋天直到1848年年底,每月的首主日,都在青年中心的四周,高舉著這細小的聖人塑像,舉行細小的聖像出遊。
在聖母的慶節日和遊行時,便使用「憂苦之慰」聖母聖像,以27里拉購於1847年9月2日,擺放於差不多在講道臺前的壁龕裡,今天,這座聖母像仍在,成為這座小堂保存下來唯一一件的紀念品。
在牆邊擺放了十四處苦路,以12里拉購回,於1847年4月1日(聖周星期四)被祝聖。在那個機會上,首次舉行苦路神功,所用的經文是鮑思高神父為青年們和大眾所編寫,並刊印於《青年袖珍》裡的,那是一冊專為青年們所編寫的祈禱書,只是在數月前才編製成的。
自最初在聖五傷方濟堂的聚會開始,聖歌在青年中心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所以,鮑思高神父購置了一座細小的風琴,為伴奏著青年的歌聲;他於1847年11月5日以35里拉購得了那座小風琴。
聖堂內的傢俱都很簡陋:24張板凳和兩張跪凳,窗戶塗上玫瑰色,數個花瓶和一盞擺放在祭堂旁的水晶燈。(參ODB 67-75)
為表示小堂的存在和每日青年中心作息時間的準則,就在樓頂上擺設了一個鐘樓,內置一個重約22公斤的銅鐘,是Vola神學家於1846年11月送贈的。(參ODB 96)
在小堂後面的兩間小房,每間房間都有一扇窗戶,一個面向操場的大門、一個小壁爐和木製的煙囪罩。過了一段時間,因著小堂不夠應用,打掉第一個房間的牆壁,將小堂伸延,將原來的第二個房間改建為祭衣所。
由畢納地棚屋改建成的小堂一共用了六年,直到1852年6月20日,即新建的聖方濟沙雷氏堂落成為止。那地便改為自修室和休憩室,甚至成為宿舍,直到1856年為止,最後,將整座畢納地房子拆掉。
在青年中心發生的事件
雖然十分簡樸及窮困,但青年中心始終能夠找到一個永久的地點:來青年中心的人數逐漸增多,很多是被隆重的儀式所吸引,另一些被音樂或遊戲所迷住:有著數名神父來協助,他們曾在數月前離開,現在都回到鮑思高神父身邊來協助他。
|
|
 「我們是這樣舉行禮儀的。在慶節日子上,一清早就打開堂門,開始聽告解,一直到舉行彌撒聖祭時才停止。彌撒的時間,原來定在八點;可是,為了滿足那些願意辦告解者的願望,屢次要把彌撒延遲到九點鐘,甚至延遲到更晚的時候。如有別的神父,那麼有一位管理學生,並與他們對答著唸經。那些已有充份準備的青少年,就在彌撒中領聖體。彌撒完畢後,我脫去了祭衣,就登上一個低小的講道臺,解釋福音;不過,當時已經開始把解釋福音,經常改為講解聖經史略。這種簡單平易的講解,加上時期,地點和名稱等比較,不管是小孩也好,或是大人也好,甚至於連那些在堂聽講的神職人員,都很歡迎。講道後,接著上課,一直到中午。 「我們是這樣舉行禮儀的。在慶節日子上,一清早就打開堂門,開始聽告解,一直到舉行彌撒聖祭時才停止。彌撒的時間,原來定在八點;可是,為了滿足那些願意辦告解者的願望,屢次要把彌撒延遲到九點鐘,甚至延遲到更晚的時候。如有別的神父,那麼有一位管理學生,並與他們對答著唸經。那些已有充份準備的青少年,就在彌撒中領聖體。彌撒完畢後,我脫去了祭衣,就登上一個低小的講道臺,解釋福音;不過,當時已經開始把解釋福音,經常改為講解聖經史略。這種簡單平易的講解,加上時期,地點和名稱等比較,不管是小孩也好,或是大人也好,甚至於連那些在堂聽講的神職人員,都很歡迎。講道後,接著上課,一直到中午。下午一點鐘,開始遊戲,有木球、高蹺、木鎗、木劍,以及最初的運動器具。兩點半,開始講解要理。一般地來說,對於教理,都一無所知。好幾次,我開始唱「聖母經」;在堂四百來個青少年,卻沒有一個會答唱的;如果我停唱,他們就唱不下去。
講解要理後,由於其時孩子們還不會唱晚經,所以就唸玫瑰經。到了後來才開始唱 “Ave Maris Stella”(萬福光耀海星),再後來唱 “Magnificat”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更後才會唱其他的聖詠 “Dixit” (聖詠109),到了最後才也會唱對經。這樣,經過了一年的學習,終於我們會唱全部的聖母晚經。在舉行了這些敬主神功之後,接著有一篇簡短的訓話,大多數講的是一個故事,把一種罪惡或一種美德予以人格化。然後以唱聖母禱文和望聖體降福來結束一切。
出了聖堂之後,各人可以開始隨意自由活動:有的繼續聽講要理,有的學唱歌或識字;不過,大多數的孩子,都喜歡跳躍奔跑,作各種遊戲。 [……]
天快黑時,鈴聲一響,大家都集合在聖堂裡,同唸一些經文,或唸玫瑰經和三鐘經,然後唱 “Lodato sempre sia” (願常受讚美),一切才告結束。
出了聖堂,我在他們中間,陪他們走。他們則唱歌或歡呼。走上了浪淘之後(Rondo),再唱幾節聖歌,彼此相約下主日再會,高聲互祝晚安,然後各自回去。」(《母院史》181-185)
|
在小堂和棚屋裡的經驗,逐漸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在初創時期,多名人物曾到訪青年中心。柏老祿侯爵夫人常關心地跟進鮑思高神父的工作,同時也對他的工作感到興趣,好於1846年夏天曾到訪那裡,看到當時環境的惡劣和可憐,再次想說服鮑思高神父返回濟良所和小醫院那裡工作。
在1848-1849年間,當鮑思高神父再一次被大部份的合作者,因著政治的理由而遭離棄時,他接待了兩位與他相識的神父,其中一位就是出名的安道.羅思彌宜(Antonio Rosmini)神父。他們見面的方式卻十分有趣:
|
|
 「當我正要開始講解要理,忙著編排班級的時候,那兩位態度謙虛而恭敬的司鐸,前來向我道賀,並詢問有關我們這個機構的起源及其組織的體制。 「當我正要開始講解要理,忙著編排班級的時候,那兩位態度謙虛而恭敬的司鐸,前來向我道賀,並詢問有關我們這個機構的起源及其組織的體制。我卻只是這樣回答道:『請你們兩位好心幫助我一下吧!你這位請到唱經所裡來,給那些年齡較大的孩子們講一講吧!』
接著我又給身材較高的那位說道:『我就把這些最頑皮的孩子交給你這位吧!』
後來我發見他們對於要理都講得非常好,就要求一位給我的青年講一篇簡短的道理,另一位給我們聖體降福。兩位都殷勤地答應了。
那位身材稍微矮小的,原來就是愛德會的創辦人安道.羅思彌宜院長(Antonio Rosmini);第二位就是公禱司鐸戴高登濟(De Gaudenzi),現在是維吉瓦諾的主教。從此以後,兩位對於本院都表示友好,而且還是本院的恩人。」(《母院史》225-226)
|
但同時也不缺乏那些不懷好意者的探訪:曾有一段時期,賈富侯爵曾派來警察。
|
|
 「每逢主日,他【賈富】都派遣幾名警察,來同我們整天在一起,在聖堂內外各地,監視一切的言語和行動。 「每逢主日,他【賈富】都派遣幾名警察,來同我們整天在一起,在聖堂內外各地,監視一切的言語和行動。
一天,賈富侯爵問一名警察說:『在那群亂民之中,你究竟看見了或聽到了什麼?』
『侯爵大人,我們看見很多兒童,在那些玩種種遊戲;在聖堂裡,我們聽見了一些令人害怕的道理;講的是關於地獄和魔鬼的事,使我也願意去辦告解。』
『關於政治呢?』
『關於政治,一些也沒有提到;因為那些孩子根本不會聽得懂這樣的話。』
(《母院史》188)
「的確,鮑思高神父很會把握時機,就趁那些警察前來監視的時候,向他們灌輸宗教的思想,講一些萬民四末的道理,從而激發他們改過遷善,善盡教友的本份。【……】
可惜我沒有把當時的情形叫人拍攝或描繪下來,不然的話,那將是一幅很美妙的圖畫。大家可以看到好幾百個青年,坐著留神地聆聽我的道理,而六個身穿制服的警察,兩個兩個地分別站在聖堂裡三個不同的位置,交叉著手臂也在聽我講道。他們雖是前來監視我,實際上卻是替我看管那些孩子,幫了我很大的忙。然而更美妙的,還是看到以下這些情景:那些警察有的用手背偷偷抹拭眼淚;有的用手帕遮掩自己的臉,以免被人看出他們感動的神情;有的則同其他孩子一起排隊輪候,到我面前來辦告解。因為當時我所講的萬民四末道理,主要是針對他們,而非針對青少年而講的。」(《聖鮑思高傳》(姚)貳、14)
|
在畢納地小堂裡所提供的宗教教育和要理講授,確實有良好的成效。讓鮑思高神父開始在年紀較大的青年中間,選定一些來分享他的宗徒使命。就在1848年,便開始傳統的「退省神功」。
|
|
 「我使用一切的方法,也是為了一個特殊的目的,就是想研究、認識和選擇幾個具有適當條件和性向,可以過團體生活的青少年,把他們收留在我家裡。同樣為了這個目的,就在那一年(1848)裡,我曾嘗試了舉辦一次小小的避靜。」(《母院史》212) 「我使用一切的方法,也是為了一個特殊的目的,就是想研究、認識和選擇幾個具有適當條件和性向,可以過團體生活的青少年,把他們收留在我家裡。同樣為了這個目的,就在那一年(1848)裡,我曾嘗試了舉辦一次小小的避靜。」(《母院史》212) |
就在初創時期的末聲,可見到上主對青年中心的祝福,其中可見一些特殊的標記,猶如在1848年慶祝聖母瞻禮時,增加聖體的奇跡(參:《鮑思高行傳》叁441-442【意】),或在1849年11月,就在畢納地小堂前,增栗子的奇跡(參:《鮑思高行傳》叁575-578【意】)。
於1856年完全拆掉畢納地房子及小堂,為興建一座更穩固及寬敞的屋子。這個曾是小堂的地方,也曾作為鮑思高神父和首批慈幼會士的餐房,就在這簡陋的餐房內,鮑思高神父曾接待了許多到訪的朋友和恩人,其中包括了Giuseppe Sarto和Achille Ratti,他們日後分別成為教宗比約十世和比約十一世(參:ODB80)。修會總部的長上將該地作為餐房直到1927年,就在該年,鮑思高神父的第三位繼任人 – 李納德神父(Filippo Rinaldi)希望將這地方,重新改建為小堂,為紀念青年中心最初期的小堂。
該小堂於1928年1月31日被祝聖,雖然不太正當,但直到今天仍被稱為「畢納地小堂」,奉獻該堂於復活的基督,為紀念1846年的復活節。.
在祭台的牆壁上,由畫家Paolo Giovanni Crida繪製了復活的基督像,讓人們記起1846年的復活節,鮑思高神父祝福這座畢納地小屋。「復活基督」正是華道角青年聖德的圖像:一個免自罪惡,及在復活之主的恩寵下重生的,滿懷喜樂及光明的生命。
祭台則由建築師Valotti設計,由四條鎬瑪瑙柱來支撐著祭台;祭台底下有鑲嵌畫,有為人類的得救而自作流血犧牲的無玷羔羊的圖像;他是葡萄樹幹,而宗徒們是樹枝,繪畫出天使和殉道宗徒的圖像,並寫上 “Euntes docete omnes gentes, praedicate evangelium universo mundo.”(解:你們要到普天下去,教導所有的民族,宣講福音。)由銅製造的聖體櫃有「魚及厄瑪奴爾」作為圖像,指出聖體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象徵,是由米蘭Beato Angelico基督宗教藝術學院所製。
在祭台上方的穹頂,以聖體圖像作為裝飾,寫上: “Haec dies quam fecit Dominus: exultemus et laetemur in ea.”(解:這是上主所選定的一天,你們要歡欣鼓舞。)是為紀念復活的喜樂和1846年復活節所帶來的歡欣。聖體欄杆以葡萄及麥穗的圖像作為裝飾,透過人類辛勞之後,聖體祭宴成為「永生的食糧」 - 這是鮑思高神父每日生活的靈修及常規勉人們「勤領聖體」。
在面對祭台的穹頂上方,則寫上《復活節繼抒詠》(Victimae paschali),並在這穹頂上繪上了七件聖事的圖案。告解聖事擺放在中央,因為鮑思高神父視它為靈修生活的鑰匙,並寫上「天門之鑰匙」(Claves Regni Coelorum)。
位處於小堂中間的第二排穹頂,寫上了復活節的對經:《天上母皇》(Regina coeli),和瑪利亞童貞作為諸德之榜樣的圖案。其中有代表耶穌的母親之童貞的圖案:熱切的愛心、與主密切的契合、及心心相印;免受罪惡的玷污、常順從主旨及童貞的生育。在拱頂中央有荊棘中的百合花的圖像,代表著鮑思高神父重視潔德,透過聖母的助佑,必能獲得的德行。
在面向祭台的右方,擺設了憂苦之慰聖母像,那是鮑思高神父於1847年所購置的:這是唯一自畢納地小堂那裡保留至今的物品。當在1856年,畢納地小屋被棄置後,鮑思高神父將這尊聖母像,送贈給他的一位修院時的好友 – Francesco Giacomelli神父,他將這聖像放置在小醫院裡,因為他當時是該處的神師。於1882年將他帶返其祖家 – Avigliana,在那裡擺放了46年之久,於1929年再次送回給慈幼會士。
四周都刻上基督及瑪利亞的稱號,以野玫瑰及西番蓮圍繞著四周,表達藉著愛,痛苦亦能產生善果。源自於祭台,小堂的四周有多個小型十字架:代表著我們每日生活上的十字架,連同耶穌的十字架,作為個人的淨化和基督徒的變化。
在聖堂背面的牆上,原是小堂的入口,擺放了一塊精緻的石碑,紀念青年中心的流徙過程。另一塊在牆壁左面的石碑,紀念鮑思高神父招待了Achille Ratti,當他成為教宗後,宣告鮑思高神父的聖德,冊封他為聖人(1934年4月1日)。第三面石碑紀念鮑思高神父曾在這裡「祈禱和獻祭 – 教導他的青年們上天的奧秘 – 之後用了約三十年的時間 – 在這四面牆壁內 – 與他的神子們分享 – 來自上天的食糧 – 給予他們天上的美味 – 同時也感受到他父愛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