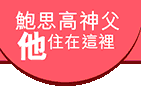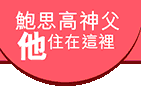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
鮑思高神父於1846年6月5日從Pancrazio Soave租賃三間在二樓隔壁的房間。在租約裡規定每個房間每月的租金為5里拉,從1846年7月1日至1849年1月1日止。聖人決定永遠離開柏老祿侯爵夫人的事業,因為他不能夠同時完成兩個職責,遠見青年中心再不是每主日的聚會,而逐漸成為較具規模的事業。
1846年春夏之間事件
當建立了小堂後,鮑思高神父將他最大的精力來鞏固青年中心的工作,但卻沒有疏忽到小醫院裡的工作,和其它許多的牧民工作。他的健康明顯地衰弱,而柏老祿侯爵夫人很衷心地關心著,決定要進行干預。她邀請鮑思高神父重新調整他過度的工作,並寫給包萊神父一封長信(1846年5月18日),來說明她的想法:不想結束青年中心,但怕鮑思高神父的生命卻要結束呢!她寫道:
|
|
 「當他在數星期前搬進與你同住後,濟良所的長上和我本人都意識到他的健康使他再不能工作了。你會記起我曾多次請你告知他要多照顧自己及休息,但你卻沒有聽從,更說神父有他要做的工作,等等。 「當他在數星期前搬進與你同住後,濟良所的長上和我本人都意識到他的健康使他再不能工作了。你會記起我曾多次請你告知他要多照顧自己及休息,但你卻沒有聽從,更說神父有他要做的工作,等等。
鮑思高神父的健康每況愈下,直到我往羅馬為止,雖然他口吐鮮血,卻仍然工作。之後我收到你的來信,告知我鮑思高神父不能再繼續履行他被聘任的工作,我立刻回應稱會繼續給予他薪酬,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他休息,而我願意立刻履行我的應允。神父,你認為聽過百青年的告解和講道,那不是工作嗎?我相信對他的健康做成很大的傷害,我覺得他應該遠離都靈,免致他的肺炎情況再差!【……】
神父,你是一位善良的人,我深信你對我很有意見,一如你曾告知我,因為我反對鮑思高神父每主日向這些青年們講解要理,和在周日的時候去照顧他們。我深信這樣的工作確實十分好,和很值得去做;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覺得鮑思高神父的健康不容許他繼續這樣的工作,另外,我覺得這些青年們以往在濟良所門外等待鮑思高神父,而現在卻在醫院的門外等他呢!
【……】
總結來說:
- 我贊同和讚賞為青年們的教導工作,但因著我們這類的住宿者,我反對這些男生們在我的機構門前聚集。
-
我深信鮑思高神父需要完全的休息,因為他衰弱的肺部,但我卻不會給予他極之需要的薪俸,除非他答應遠離都靈市,不從事任何傷害他健康的事情。這為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神父,我明白我們之間在這方面有分歧,為我的良心,我常願意接受你的批評!【……】
(《聖鮑思高傳》貳、360-361【英】、464-466【意】)
(《聖鮑思高傳》貳、360-361【英】、464-466【意】)
|
到了五月底,侯爵夫人看到之前所做的工作都沒有什麼效果,要求鮑思高神父要作出抉擇:若他繼續想受聘的話,就要停止他目前為青年中心工作的生活節奏。但這位年輕的神父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回答說:「侯爵夫人!我已經考慮過了。我奉獻了我的生命,為謀求青年們的福利。我感謝夫人妳給我所作的提議;可是,我不能放棄天主上智給我所指定的路線。」(《母院史》154)
他於是在1846年8月底終止了作為小醫院神師的工作。
過了不久,一如侯爵夫人所預見的,鮑思高神父的健康開始變差:
|
|
 「當時我擔任許多工作;或在監獄裡、或在高道倫可醫院裡、或在慶禮院和學校裡。這些繁忙的工作,迫使我不得不利用夜裡的時間,來編寫我所絕對需要的課本和用書。我的健康已很弱,因過度疲勞,而竟這樣惡化,以致醫生勸我停止一切工作。神學博士包萊很愛我,為了我的益處,送我到沙西的本堂神父那裡去住一個時期。我在一周合休息,到了主日,我回慶禮院工作。但是,這不足以解決問題。青少年們成群地來訪問我;除了他們以外,還有當地的那些青少年。因此,我在那裡,比在都靈更不得安寧;而且也給我的小朋友們增加了很多痳煩。」(《母院史》194-195) 「當時我擔任許多工作;或在監獄裡、或在高道倫可醫院裡、或在慶禮院和學校裡。這些繁忙的工作,迫使我不得不利用夜裡的時間,來編寫我所絕對需要的課本和用書。我的健康已很弱,因過度疲勞,而竟這樣惡化,以致醫生勸我停止一切工作。神學博士包萊很愛我,為了我的益處,送我到沙西的本堂神父那裡去住一個時期。我在一周合休息,到了主日,我回慶禮院工作。但是,這不足以解決問題。青少年們成群地來訪問我;除了他們以外,還有當地的那些青少年。因此,我在那裡,比在都靈更不得安寧;而且也給我的小朋友們增加了很多痳煩。」(《母院史》194-195) |
七月初的一天,一群來自基督修士會學校的400位學生來到沙西,想辦告解。鮑思高神父連同當地的神父們一起來聽他們的告解,但這樣勞累使鮑思高神父終於倒下:
|
|
 「我回到了自己的寓所,全身虛弱無力,就被放在床上。起初發見的疾病是氣管炎,加上劇烈的咳嗽。只有八天,別人以為我已到了生命的終期。我就領了臨終的聖體,也領了病人傅油聖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死去,只庛到遺憾的,就是要拋下我的那些孩子;不過,我稍可引以自慰的,就是在我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前,能夠眼見慶禮院已有一個固定的形態。」(《母院史》196) 「我回到了自己的寓所,全身虛弱無力,就被放在床上。起初發見的疾病是氣管炎,加上劇烈的咳嗽。只有八天,別人以為我已到了生命的終期。我就領了臨終的聖體,也領了病人傅油聖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死去,只庛到遺憾的,就是要拋下我的那些孩子;不過,我稍可引以自慰的,就是在我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前,能夠眼見慶禮院已有一個固定的形態。」(《母院史》196) |
青年中心的青年們得悉鮑思高神父將要臨終時,因著對這位朋友的極大愛情,立刻熱誠地祈求:
|
|
 「他們自動祈禱、守大齋、聽彌撒、領聖體。他們也互相輪流著日夜在憂苦之慰聖母像前唸經。早上他們點著特別的燈,一直到深夜,常有許多孩子,苦苦哀求天主的偉大母親,給他們保存這個可憐的鮑思高神父。 「他們自動祈禱、守大齋、聽彌撒、領聖體。他們也互相輪流著日夜在憂苦之慰聖母像前唸經。早上他們點著特別的燈,一直到深夜,常有許多孩子,苦苦哀求天主的偉大母親,給他們保存這個可憐的鮑思高神父。
有好幾個孩子許願要一個月內每天唸十五端玫瑰經,有的許願要唸一年,有的甚至於許願終身要這樣唸玫瑰經。也有些孩子許下要一連幾個月守大齋,有的許下要一連守幾年,甚或一生常守大齋,只吃麵包和喝清水。我知道,有好幾個做泥水匠的青年小工,一連幾個星期守大齋,只吃麵包,喝清水;可是,他們從早至晚,絲毫不減他們那種沉重的工作,而且一有了少許空餘的時間,立刻前往至聖的聖體面前祈禱。
天主俯聽了他們的禱聲。那是一個星期六的黃昏。人人以為那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個晚上。來會診的醫生都這樣說,我自己也這樣想,因為覺得全身沒有一些力氣,而且在不停地出血。到了深夜,我覺得想睡,後來就睡著了。醒來時,已經沒有了危險。」(《母院史》196-197)
|
為能恢復體力,我聽從勸導,返回碧基村休養了三個月。在離開之前,於八月初,我從Pietro Clapie那裡,即從蘇亞維那裡,租賃在二樓的第四間房間(參:《鮑思高言行錄》貳、500【意】)。包萊神父負責監督裝修的工程,好讓鮑思高神父能夠遷往那裡居住。
在這段期間,每主日的聚會和學校在包萊神父的負責下繼續下去,同時得到Vola和Carpano神學博士,與及Trivero和Pacchiotti神父的協助。
遷往畢納地小屋
鮑思高神父於1846年11月3日結束了他在碧基村的休養後,遷回畢納地四個房子的小屋裡去,與他同時到來的,有媽媽麗達;她決定跟隨她的兒子,因為她目前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也沒有什麼家當,為了照顧她的兒子,及協助他的牧民工作。她臨在於華道角,也可說是比較明智的決定,特別是居住在那區域的人們,特別是她的兒子決定收留第一批的孤兒時。
這四個房子都是十分簡陋和不牢固的。而小堂和房子的每年租金為600里拉;另外還有每日生活的開支、節日的支出、抽獎、茶點和給予青年中心較窮困的青年的金錢幫助。他將一切都交付在天主上智的安排,和其它方面的幫助。從包萊神父的筆記簿中,我們得知賈法束神父支持租金,同時也有來自其它神職人員和教友的捐助;而柏老祿侯爵夫人仍然以「無名氏」身份,或透過賈法束神父來繼續支持鮑思高神父的工作。
經濟上的困難並沒有使鮑思高神父氣餒,他更擴展他的工作。就在這環境下,於1846年12月1日租下整座畢納地房子和周圍的土地。然而,蘇阿為仍然保存他在樓下的工作間,直到1847年3月1日止。當與蘇阿為的合同結束後,包萊神父再次就畢納地的產業,簽定新的合同,是由1849年4月1日至1852年3月31日為止。畢納地在合同裡稱,為了支持這項慈善事業,每年的租金只為1,150里拉。於合同結束前的一年,即在1851年2月9日,方濟.畢納地以28,500里拉的價錢,出售與「若望.鮑思高神父、若望.包萊神父、Roberto Murialdo, 若瑟.賈法束神父,那塊位於斐利伯兄弟相鄰的東面和xxx、在園戶街的東面,Bellezza的西面的土地。」(ODB 99)
小屋的狀況
|
|
 「屋子的正面朝南,只在這朝南方向有門及窗戶。住所部份包括有地下及十分矮小的二樓,包括了目前聖方濟.沙雷氏小堂的走廊,大約有20米長,6米寬。整座房子的高度不超過7米。 「屋子的正面朝南,只在這朝南方向有門及窗戶。住所部份包括有地下及十分矮小的二樓,包括了目前聖方濟.沙雷氏小堂的走廊,大約有20米長,6米寬。整座房子的高度不超過7米。「在面向樓梯,有一個狹窄的門,可以進出;在朝東的牆上,設有一個由石鑿出來的水池,可以取用清澈的泉水。這座房子有多個房間。在樓下,就在水池的後面,在一個長方型和有單一窗戶的房間裡,有一個細小的拱廊,那裡成了鮑思高神父和他早期合作者的餐房。
「在那通往二樓的木製樓梯,由畢納地所建,日後由鮑思高神父改以石造的梯子,左轉便是與樓下餐房對應的房子,前面有木製的走廊,貫穿整個上層,在那裡有門可以進出四個房間,而每個房間都有窗戶;樓下也有同樣的房間安排。屋頂上有一個天窗,可以透光及通風;大約在屋子的中間部份,有一個細小的地窟。
「在居住的房間背後,就是那由棚屋改建的小堂,有著同樣的長度及寬度。
「在畢納地屋子旁,就是現在有走廊的地方,自開始便是一個操場,那裡是一片低洼而又十分空曠的地方。
「兩翼的房子都是一樣的,那朝東的有一扇門及窗戶,最早期作為馬棚,後改建為房間;而朝西的則用作堆柴間。
「上面作為堆草房。【…】
「鮑思高神父重新簽定這份租約合同,由1849年4月至1852年3月止,這包括了朝西的一塊空地。這可以說是青年中心的首次擴建,即在建聖方濟沙雷氏堂之前的擴建。這是為給青年人活動休憩的空間。
「於1849年夏天,鮑思高重修這破舊的房子,那包括那朝東的,曾用作堆柴用的,作為牲口用棚子,也是唯一較寬大的房子,現改建為一個小禮堂,可作演戲用;但特別是為了天氣較壞的時候,不能在小堂外的空地聚會時使用的。」(ODB 100-102)
|
四周環境及空地
畢納地房子四周的空地,約有3,697平方米,大部份都種植了樹木。
位於小堂旁,朝北的空地(參圖 (1))長約六十多米,但只寬八米,是青年中心的第一個操場。
朝西,即小堂的入口處,即今天的聖方濟.沙雷氏堂的地方,是一塊不規則的空地(參圖 (2)),面積約為30米乘20米,是鮑思高神父作為青年休憩的中心,在那裡設置了鞦韆和蹺蹺板,和一些體操的器材。
而朝東的那片空地,即那位於棚屋和斐理伯兄弟草地之間的空地(參圖 (3)),保留作為免子的飼料場。
最後,在畢納地屋子前(參圖 (4)),一片較大的空地,作為菜園(參ODB 102-104)。這裡後來稱為「媽媽麗達菜園」:是天主為這位善良的婦女所保留的,她細心地照顧這片菜園。日後為了給青年們更多活動的場所,便刪除了這片菜地,因為當孩子們熱衷於遊戲時,常侵擾這地方;特別記錄了於1848至1849年那「愛國運動」期間,由那稱為狙擊手的布羅肖(Brosio)組織的「軍事演習」和「戰爭遊戲」裡,孩子們大事蹂躪了那片菜園呢!(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439-440;【中】《聖鮑思高傳》(姚)貳、155-156)
鮑思高神父於畢納地屋子的房間
我們並不清楚,鮑思高神父於1846年11月遷進畢納地屋裡時,住在樓下四間房子裡的那一間。但我們可以肯定,過了不久,因著晚上一些奇怪的聲音,他遷往向東的第一個房子,一直到畢納地屋子被拆卸為止(1852)。但晚上怪聲的騷擾在新的房間裡仍然繼續,使他無法入睡;直到最後,鮑思高神父將一幅聖母聖相安放在閣樓上,騷擾才停止。(參:【中】《聖鮑思高傳》貳、56)那個地方也作為他工作學習和接見客人的地方。在門外橫額上寫著一道短誦:「願耶穌基督受讚美」。(“Sia lodato Gesu Cristo”)
鮑思高神父就在這個房間,做了那個著名的《玫瑰花棚》的奇夢。鮑思高神父看到他的事業和他的合作者怎樣為了青年們的利益而工作,好像踏上了一條長路,在開始時顯得十分輕鬆容易,但事實上卻有許多困難(長在玫瑰花下的剌);但因著童貞聖母的指導和注重牧民愛德上(玫瑰花代表著),鮑思高神父和他的合作者都有勇氣繼續跟隨這路徑,並完成托付給他們的使命。(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32-37;【中】《聖鮑思高傳》貳、58-60)
麗達媽媽曾居住在兒子隔壁的房子裡(《鮑思高言行錄》叁、228-230)
畢納地屋子時代的青年中心的組織及發展
當青年中心找到了一個永久及穩固的基地後,可以讓鮑思高神父反省及評估過往的經驗,特別在組織、紀律、培育和管理的各個層面:
|
|
 我在華道角定居之後,凡能有助於維持精神、紀律和管理,使其統一的事項,都悉心加以推動。首先我編修了一份規則,把慶禮院裡所實行的事,以及應該按照同樣實行的方式,都在這份規則裡簡要地陳述出來了。……這本小小的規則,卻有很大的用處:各人都可以藉此知道自己應該做的事。由於我經常讓每一個人負責他自己的那份職務,所以各人都用心認識自己的本分,而努力盡好。(《母院史》202) 我在華道角定居之後,凡能有助於維持精神、紀律和管理,使其統一的事項,都悉心加以推動。首先我編修了一份規則,把慶禮院裡所實行的事,以及應該按照同樣實行的方式,都在這份規則裡簡要地陳述出來了。……這本小小的規則,卻有很大的用處:各人都可以藉此知道自己應該做的事。由於我經常讓每一個人負責他自己的那份職務,所以各人都用心認識自己的本分,而努力盡好。(《母院史》202) |
自1847年起,鮑思高神父開始在他的事業中採用《慶禮院規則》,逐步改善,若干年後,終於在1877年將它刊印成冊(OE 29, 31-94)。在編輯這規則時,他也加註了其他的文獻:一些比較古舊慶禮院的規則,例如是聖斐理.納內(Filippo Neri)和聖嘉祿.包祿(Carlo Borromeo)慶禮院的規則,和一些當代的經驗。其中主要有研究《於1842年建於米蘭的聖磊思青年中心規則》(“Regole dell’Oratorio di S. Luigi eretto in Milano nel 1842”)和《以聖家作主保的青年中心規則》(“Regole per I figliuoli dell’Oratorio sotto il patronato della Sacra Famiglia”)。但這些青年中心的規則其不完全適用,因為他所面對的孩童及青少年,需要一種新的方法及規則。他刪除了那些已過時的安排,和其它所有強迫性的宗教本分,例如:告解紀錄、強制性的領聖體、每班輪流辦告解和只將早餐給予那些領了聖體的青年。
整份文件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青年中心的宗旨,和與院長合作的其他職務;第二部份是宗教的神業工作,即青年們應該有的本分,和在聖堂內外的合適表現;第三部份是日後加上的,有關於日校及夜校的規則,和一些總則。
其中一份特殊的規則,是在同一月份的,是有關一群特別的青年,是有關《聖磊思善會規則》也包括在內,法蘭騷尼總主教於1847年4月12日批准這份規則,也加進入整份青年中心規則內(全文可見【意】《鮑思高言行錄》叁、216-220)。
鮑思高神父特別關心去安排青年們的「祈禱生活」,希望給予當時的青年們一種新穎及容易使用的祈禱手冊:《青年袖珍》(“il giovane provveduto”)(Paravia 1847),就在聖人在生時,已再版122次。
在這些宗教神業工作裡,最值得提及的,是自1847年開始便有的「習練善終」,這成了慈幼會青年工作中最具特色之一,一直維持到現在。在每個月的首主日,安排青年們辦告解及領聖體,好像是一生中最後一次領受聖事一樣,和團體一起誦唸經文,求天主賞賜免於猝死,為使這主日與其他主日的不同,該主日彌撒後,各人分發到一份豐盛的早餐(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19)
節慶日在青年中心也是重要的,在宗教方面有:以九日敬禮來準備、善領告解及聖體聖事、及立定善志;而同時也安排餘慶節目:下午有特別的遊戲、映畫戲、氣球、煙火、音樂演奏和戲劇、參觀名勝和抽獎。所有這些活動,都來表達在天主的恩寵中,享受這份喜樂。其它也有基督徒的傳統節日,差不多每一個月都有特殊的慶祝活動:聖方濟.沙雷氏、聖磊思.公撒格、護守天使和聖母的慶日(領報 、升天、誕辰、玫瑰聖母和無原罪聖母)。
除了團體公唸的經文外,亦留下一些自由空間,鼓勵青年們在個人的靈修生活上有所成長。例如:朝拜聖體、神花和不同的禱文。為那些較成熟的青少年,鮑思高神父為他們安排「退省神功」:首次是在1847年舉行,由年輕的Federico Albert神學博士主持講道,他日後成了都靈市Lanzo的本堂神父,現已被列入真福品。
在畢納地小屋的房子內,曾漸進式地開辦了主日學及夜校,在逐漸成熟的環境下鞏固下來。鮑思高神父除了編排那些傳統的課程外,也加進了算術、設計、十進制和唱歌與音樂。
當時有些學校採用的,是當時比較前衛的教育方法。他們有來自政府、教育家、和有興趣提開平民大眾的人士,他們共同研究和以實踐來証實它的效果。鮑思高神父在他那方面,讓別人認識和宣傳這類學校,深信它們為青年勞工的重要性。就在1847年的上半葉,得到他的同學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都是該市的教育家和老師:Aporti院長、il Boncompagni, il Prof. Giuseppe Rayneri, il teologo Pietro Baricco, 辣沙兄弟會會長Michele修士和其它人士。他們有了好的開始,翌(1848)年,市政府的Regia Opera della Mendicita Istruita 採用了華道角的教育方法,也開辦多所夜校。後來亦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審查那些採用這個教育法的學校和青年中心的成效,並每年撥款300里拉作為資助,一直到1878年為止(參:《母院史》219-220;【意】《鮑思高言行錄》叁、26-28)
鮑思高神父除了照顧這些學校之外,亦需要為學生提供相關的教科書:《教會史 – 學校用書》(“Storia ecclesiastica ad uso delle scuole”) (1845)、《簡易的十進制 – 適用於工藝生及農民》(“Il sistema metrico decimale ridotto a semplicita … ad uso degli artigiani e della gente di campagna”)(1846)、《聖經史 – 學校用書》(“Storia sacra per uso delle scuole”) (1847)和日後刊印的《意大利歷史 – 青年版》(“La storia d’Italia raccontata alla gioventu”) (1855)。
隨著這思潮的另一個創新點,就是著名的「歌詠班」。當開始教導歌唱宗教歌曲後,鮑思高神父立刻也開始教導他們有關音樂的知識,編纂合適的教學海報:「由於當時(1845年)在學校裡上音樂課,還是一種創舉,所以同時給許多人一起在課室上音樂課時,有很多人都來聽課。那些有名的音樂家,如磊思.羅西(Luigi Rossi)、若瑟.布藍基(Giuseppe Blanchi)、謝魯諦(Cerutti)、公禱司鐸磊思.那西(Can. Luigi Nasi)等,每天晚上,都急急地前來聽我的課。……他們之來旁聽,是想觀察怎樣實行新的教授法。其實它只不過就是如今在我們的學校所實行的方法而已。」(《母院史》207-208)
在一些節慶日和晚上,鮑思高神父也得到一些年輕學生的協助,我們在前面已談及過的。青年中心特別在星期四下午開放給他們,讓他們有機會複習、和提供娛樂及受培育的機會。當時來青年中心來的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多,因此,他們也成了青年中心要受關注的另類青年。他們當中有些教授要理,和給予鮑思高神父大力的協助;在傍晚時候,鮑思高神父聚攏這首批「合作者」,和他們一起準備下主日的要理教授的內容和活動。(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175-176)
畢納地屋子的新客人
都靈市的社會環境是十分惡劣的,許多從鄉間來的季節小工和孤兒們在晚上都找不到一處安身之處。大、小旅館的馬棚、茅舍和工地的儲藏室、貧瘠的屋頂等地方,都可以找到這些好像難民一樣的青年們,他們的衛生環境及道德狀況之差,可想而知。
鮑思高神父除了研究怎樣處理這個迫切的問題外,他在堆草房裡也準備了一些簡陋的床鋪、一些乾淨的稻草,也提供床單和毯子。但從他的客人中所得到的回報卻是:「不料他們有的把被單帶走,有的則把毯子拿去,有的甚至於把乾草也偷去賣掉。」(《母院史》204-205)
他需要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這一次猶如祿茂.夏來理一樣,在不經意之下,開展了日後成為慈幼會事業中一項穩固及具特色的工作。
|
|
 一個五月的晚上,天在下雨,夜已深,忽然來了一個年約十五歲的孩子,全身都被雨淋濕了。他哀求給他一些麵包和一處過宿的地方。我母親把他帶到了廚房裡,讓他留在火爐旁。當他在烤火和烘乾衣服的時候,給他麵包和羹湯,使他充飢。同時我問他是否上過學,有沒有親戚,使什麼工作? 一個五月的晚上,天在下雨,夜已深,忽然來了一個年約十五歲的孩子,全身都被雨淋濕了。他哀求給他一些麵包和一處過宿的地方。我母親把他帶到了廚房裡,讓他留在火爐旁。當他在烤火和烘乾衣服的時候,給他麵包和羹湯,使他充飢。同時我問他是否上過學,有沒有親戚,使什麼工作?
他答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孤兒,從塞西阿谷(Valle di Sesia)來找工作的。我本來只有三個法郎;還沒有工作賺錢,卻把它們都花完了。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什麼親戚。」
「你初領聖體了沒有?」
「還沒有。」
「堅振呢?」
「也沒有。」
「辦過告解嗎?」
「有時我去辦過的。」
「現在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求你可憐我,讓我就在這屋子的角落裡過夜吧!」
說了這話,他就哭起來了。我母親也在流淚;我很感動。
「要是我實在知道,你不是一個小偷,我就替你想辦法;可是,別人已經偷去了我的一部分毯子,你要把另一部分帶走。」
「不!請你放心!我窮,可是,我從來沒有偷過任何東西。」
我母親接著說:「你願意的話,今晚上由我來安置他。明天,天主自會照顧我們的。」
「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廚房裡。」
「他連鍋子也會帶走哩!」
「我會想辦法的,免得發生這樣的事。」
「好吧!那妳就這樣辦吧!」
我的好母親,由那個孤兒幫助著,從外面搬來了一些磚,在廚房裡疊成了四根小柱子,又在上面鋪了幾塊板,板上再放了一個大痳袋,就這樣預備了慶禮院裡第一張床。後來我母親給那個孩子說了幾句勸告的話,說明人必須工作,做人要忠實,要恭敬天主。最後叫他唸經。
他回答說:「我不會。」
我母親對他說:「你跟著我們唸吧!」
我們就這樣唸了經。
為了保存一切的東西,便把廚房上了鎖,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開。
這是我們第一個寄宿生。……那是1847年。(《母院史》205-207)
|
同一年,也收留了第二位青年:他們留在畢納地房子裡直到當季工作完成為止。該年年底時,鮑思高神父已經租用了整座房子了,而寄宿生的人數也漸漸增多。同時,鮑思高神父也收留一些付得起寄宿費的宿生:來自新堡的Pescarmona騎士之子、到Bonzanino教授上課的學生、和他的兩位司鐸朋友,Carlo Palazzolo神父(鮑思高曾在基愛理協助過當時仍為管堂員)和Pietro Ponte神父。這兩位司鐸在周內執行他們的牧民工作,而在同末便協助鮑思高神父,但他們因著畢納地屋子裡的「刻苦」精神,留在那裡不到一年便離開了。(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252-253)
因著教區修院於1848年被關閉後,這裡也收留了部份的修生。他們便形成了華道角早期的三類青年:工藝生(大部份為孤兒)、讀書生和修生。
在這班早期的學生中,包括有:Reviglio和Carlo Gastini。(參:【意】《鮑思高言行錄》叁、338-345)
鮑思高神父看到這項工作的有效性後,決定大力發展,並開始擴建的工作。從此便誕生附屬於青年中心的「寄宿部」或「家舍」。
牧民策略
到青年中心來的青年人數不斷增多,許多都是因為被鮑思高神父個人魅力所吸引而來的。但他主要是尋找那些最貧窮的和被遺棄的青少年,讓他們能遠離流浪街頭,避免更大的危險。為達到這目的,他採用不同的方法,但都是經過個人的接觸和他那份觸動人心的關愛。
他多次在午飯時間,特意經過這些工廠和工地,加入學徒們的交談,與他們談起話來,對他們的問題感到興趣;另外的時候,當他遇到一群青少年正在玩牌或骰子時,便與他們一起坐下,有時更參與他們的「賭博」遊戲裡;對於那些年紀較少和頑皮的孩子,便會送給他們水果和糖果;走進他們工作的小旅館、咖啡館或理髮店裡,與僱主和學徒們交朋友,及邀請後者到青年中心去。
他們常常是在Emanuele Filiberto(今稱共和國廣場piazza della Repubblica)廣場那裡聚集,當時也稱為「宮門廣場」(Porta Palazzo)。那裡是市集的廣場,每天都聚集許多的青少年在那裡,和那些十分貧窮的青少年學徒:流動小販、售賣火柴、擦皮鞋、掃煙囪、小馬倌、雜工、搬運工和許多其他為每日生計而勞動的、窮苦的青少年。絕大部份都是住在Vanchiglia區,可以說是小型的青少年犯聚集的地方。直到1856年為止,鮑思高神父每天早上都會到這個廣場去,以不同的藉口,好去探望這些青少年。不多久,他已經能夠牢記他們的姓名,並邀請他們到青年中心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