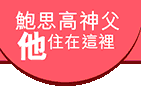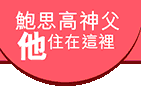鮑思高神父按照賈發束神父的建議,於1841年11月3日進入司鐸培養院。他曾這樣說道:「你必須研讀倫理學和講道學。現在放棄一切的職務,到培養院裡來。」(《母院史》113)培養院那時已遷往都靈。
在這位導師指導下,鮑思高神父在教會知識及牧民方面有所長進;及開展充滿活力的司鐸靈修;引導他,讓他逐漸明瞭、分析和面對整體的牧民現況,那是與他所來自的農村環境斷然不同。

賈發束神父教導他,使他將個人的聖德、宗徒熱誠和牧民的方法融合在一起;介紹他特別關注那些在堂區牧民工作裡被忽略的人,並使他意識到他對青年工作的特長,讓他有機會去接觸在城市中最貧窮和被遺棄的青少年。他首先聚集那些年輕的磚石工和掃煙囪童工,為他們辦要理班;他同時也在該市新興的慈善事業內服務(高道倫可、柏老祿的慈善事業、由基督修士會為貧童所辦的學校);賈發束神父也帶他一起探訪監獄;結識到Cocchi神父和其他的神父,在當時一起籌劃試辦青年中心的事宜。
有關這位導師,鮑思高神父這樣說:
|
|
 「六年以來,賈發束神父常在指導著我,他也是我的神師。如果我做了一些善事,我都應該歸功於這位有聖德的司鐸。我把自己的一切決定、一切學業、一切行動,都放在他的手中。」(《母院史》115) 「六年以來,賈發束神父常在指導著我,他也是我的神師。如果我做了一些善事,我都應該歸功於這位有聖德的司鐸。我把自己的一切決定、一切學業、一切行動,都放在他的手中。」(《母院史》115) |
感謝賈發束神父的學院和讓他所體驗出來的牧民經驗,我們的聖人開始感悟出一種教育及牧民方法:預防,特別是為那些處於危險中的青年:
|
|
 「第一件事,他帶我到監獄裡去。我在那裡,立刻認出了,人是多麼邪惡和可憐。目睹成群的孩子,年齡只不過十二歲至十八歲,身體健全,心智聰明,卻在那裡閒著,終日無所事事,被蟲豸所咬嚙,缺乏精神的和物質的食糧,真使我怵目驚心。……然而,當我發見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出獄時,曾立下了回頭改過的堅志,但不久又被送進那不過數天才出去的受刑之地的時候,我是多麼震驚! 「第一件事,他帶我到監獄裡去。我在那裡,立刻認出了,人是多麼邪惡和可憐。目睹成群的孩子,年齡只不過十二歲至十八歲,身體健全,心智聰明,卻在那裡閒著,終日無所事事,被蟲豸所咬嚙,缺乏精神的和物質的食糧,真使我怵目驚心。……然而,當我發見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出獄時,曾立下了回頭改過的堅志,但不久又被送進那不過數天才出去的受刑之地的時候,我是多麼震驚!就是在那種情形之下,我發覺,有不少犯人之所以重蹈覆轍,是因為無人照料,完全被人遺棄之故。
我心裡自忖著說:『如果這些孩子,在外面能有一個友善的人照顧他們,幫助他們,在慶節日子,教他們學習要理,誰知道他們不會改過向善?或者至少可以減少那些重入監獄的人數呢?』
我把這個思想,向賈發束神父披露了。得到了他的忠告和指導之後,我就開始研究實行這個計劃的方法,並將成果託給上主助佑的恩寵;沒有祂的助佑,只靠人力,必將徒勞無功。」(《母院史》115-116)
|
青年中心的誕生
這位年輕的司鐸對於青年工作的熱忱,在初到都靈時已表現出來了;他視之為天主的召叫,要為他們實際做些工作:
|
|
 「我剛進了聖方濟司鐸培養院,立即就有一群孩子,在市內的道路和廣場上跟隨我,甚至於也到司鐸培養院的祭衣房裡來找我。但因缺乏地方,無法直接照料他們。」(《母院史》116-117) 「我剛進了聖方濟司鐸培養院,立即就有一群孩子,在市內的道路和廣場上跟隨我,甚至於也到司鐸培養院的祭衣房裡來找我。但因缺乏地方,無法直接照料他們。」(《母院史》116-117) |
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當他到達司鐸培養院約一個月後,就在1841年12月8日 – 無原罪聖母瞻禮日上,於聖方濟堂的祭衣房內,與祿茂.夏來理(Bartolomeo Garelli)的首次會面,開展了他的事業:
|
|
 「聖母始胎無玷節日(1841年12月8日),在預定的時刻,我正在穿祭衣,準備去獻彌撒聖祭。管理祭衣房的修士若瑟.高木底(Giuseppe Comotti),看見在屋角有一個少年,便叫他來為我輔彌撒。 「聖母始胎無玷節日(1841年12月8日),在預定的時刻,我正在穿祭衣,準備去獻彌撒聖祭。管理祭衣房的修士若瑟.高木底(Giuseppe Comotti),看見在屋角有一個少年,便叫他來為我輔彌撒。
他很害羞地答道:『我不會。』
高木底又說:『快來!我要你輔彌撒。』
那個孩子再回答說:『我不會,我從來沒有輔過。』
管理祭衣房的修士就很生氣地說:『畜牲!你既然不會輔彌撒,那你到這祭衣房裡來幹什麼?』說著拿起一根雞毛帚,在那孩子的背上或頭上亂打。那孩子急忙逃避。
我高聲叫道:『你幹什麼?為什麼這樣打他?他做了什麼?』
『他既然不會輔彌撒,為什麼到祭衣房裡來?』
『可是,你做得不對。』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有很大關係;他是我的朋友,你馬上去叫他來,我有話跟他說。』
『喂!喂!』管祭衣房的開始叫,一面追那個孩子,一面告訴他,不會再虐待他,終於把他拉到了我面前。那孩子因被打而在流淚發抖。
我盡量和善地對他說:『你已經望了彌撒沒有?』
他回答說:『沒有。』
『那麼你就來望彌撒吧!彌撒後,我想跟你談談一件使你高興的事。』
他答應了我。我的用意,是想給那個可憐的孩子,稍為安慰幾句,免得那些管祭衣房的人,給他留下不良的印象。我獻完了彌撒,又唸了應唸的感謝經,便帶我的那個備取者到了祭衣房的一間小室裡。我滿露著笑容,寬慰了他幾句,叫他不用害怕,就開始這樣問他說:『我的好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祿茂.夏來理(Bartolomeo Garelli)。』
『你是什麼地方人?』
『亞斯底人。』
『你父親還在嗎?』
『不在,我父親早已死了。』
『你母親呢?』
『我母親也死了。』
『你今年幾歲?』
『十六歲。』
『你會唸書寫字嗎?』
『一點兒也不會。』
『你初領聖體了嗎?』
『還沒有。』
『你辦過告解嗎?』
『辦過的;不過,那時我還很小。』
『我不敢。』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紀比我小的同學,知道要理;我這麼大,卻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我害臊上那些班級裡去。』
『如果我另外教你要理,你願意不願意學?』
『很願意。』
『你願意到這間屋子裡來嗎?』
『我很願意,只要別人不打我。』
『放心!沒有人再會虐待你的。而且從今以後,你是我的朋友,有事來找我,誰也不得干涉你。那麼,你想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要理課呢?』
『隨你便。』
『今晚?』
『好。』
『現在就開始,好不好?』
『也可以,很好。』
我站起來,畫了一個十字聖號,準備開始;可是,我的那個學生卻沒有畫,因為他不知道怎樣畫。要理的第一課,就是教他學畫十字聖號,並使他知道造物的天主,以及天主創造我們的目的。」(《母院史》117-121) |
鮑思高神父於1885年對慈幼會士敘述了這次會晤的一個細節。在畫完十字聖號後,我們一起唸了「聖母經」。「所有來自天上的祝福都是源自於這首篇,充滿著熱誠和意向,與祿茂.夏來理一起,在聖方濟堂內所唸的『聖母經』所賜。」(《鮑聖言行錄》拾柒、510)
在這首次的見面後,每個主日在培養院中都聚集了一群青少年,數目同時也與日增多;翌年二月時約有二十餘人;三月底為三十人;在泥水匠主保 – 聖安納(7月26日)瞻禮時,已近百人。
這批在早期到青年中心來的青年人,大部份都是按季節,因農閒(自秋天後期到六月底)而來到都靈市的工人和泥瓦小工,他們一般是「薩伏亞人、瑞士人、有的是奧士達谷人、有的是比哀拉人,有的是諾瓦拉人,有的是隆巴地人。」(《母院史》142)「一般地來說,慶禮院生,有鑿石匠、石膏匠、鋪石匠、塗泥匠,以及其他的工匠,都來自遠地。由於他們不熟悉聖堂,也不認識友伴,往往有誤入歧途的危險,尤其是在慶節假期。」(《母院史》123)
這類季節移民的青少年,一直都到鮑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去,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到都靈的移民潮穩定下來。
鮑思高神父再次描寫在培養院每主日聚會的發展:
|
|
 「當時我們在司鐸培養院裡舉辦的慶禮院是這樣的:每逢慶節日子上,孩子們都有辦告解和領聖體的方便。不過,每個月都定有一個星期六和一個主日,為辦妥這些敬主神工。下午到了規定的時間,先唱一首聖歌,接著講解要理,並講一個故事,最後分派一些東西,有時給大家,有時則舉行摸彩,而給中獎的人。……
善心的神學博士挂拉和賈發束神父,都很喜歡這些兒童,很樂意地給我一些圖像、單子、小冊、聖牌和小苦像等,以便分贈給兒童們。有時他們也幫助我贈送衣服給那些比較窮苦的孩子,給另一些孩子幾個星期的糧食,直到他們找到工作,能自立謀生為止。
此外,他們因見慶禮院的兒童人數大增,便容許我有時在附近的空地上,集合我的這支小軍隊,讓他們在那裡遊戲。假如能有更大的場所的話,兒童人數也許可以多至數百人;但我們只能收八十人左右。 當兒童們去領聖事的時候,神學博士挂拉或賈發束神父,通常都來看我們,給孩子們講一個勸人行善避惡的故事。」(《母院史》122-124) |
在一周裡,鮑思高神父利用課餘時間,繼續接觸這些青少年:
|
|
 「我這樣去訪問他們,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安慰,因為他們看到,有一個友人關懷他們;對那些僱用他們的雇主來說,也感到滿意,因為他們也很希望自己能管理這樣的青少年;平日有人照顧他們,尤其是在慶節假期,因為這樣的日子更具有危險性。 「我這樣去訪問他們,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安慰,因為他們看到,有一個友人關懷他們;對那些僱用他們的雇主來說,也感到滿意,因為他們也很希望自己能管理這樣的青少年;平日有人照顧他們,尤其是在慶節假期,因為這樣的日子更具有危險性。每星期六,我到監獄裡去探訪監犯,衣袋裡裝滿著煙草,或水果,或麵包,常是為了照顧那些不幸而身陷囹圄的青少年,幫助他們,贏取他們的友情,好使他們一旦幸而出獄時,到慶禮院裡來。」(《母院史》124-125) |
以友情、輔助和個人關注,這些都是鮑思高神父用來贏取頑固青少年的方式,而他開始發展一套建基於「仁愛、宗教及理智」上的預防教育和牧民方法:
|
|
 「那些從受刑的地方出來的青年,如有一隻友善的手,肯照顧他們,在慶節日上看管他們,在証些忠實的雇主那裡,替他們找一份工作,在平日有時去訪問他們,那麼這些青年,就會過光明正當的生活,忘下自己以前的事,成為善良的教友,忠實的國民。」(《母院史》121) 「那些從受刑的地方出來的青年,如有一隻友善的手,肯照顧他們,在慶節日上看管他們,在証些忠實的雇主那裡,替他們找一份工作,在平日有時去訪問他們,那麼這些青年,就會過光明正當的生活,忘下自己以前的事,成為善良的教友,忠實的國民。」(《母院史》121) |
當結束他三年(兩年作為學生、一年為助教)留在培養院的生活時,鮑思高神父越有被召成為青年人牧者的傾向,在面對猶豫不決的事時,交托在上主手裡:
|
|
 『一天,賈發束神父叫我去見他,對我說:『現在你已畢業,應該出去工作了。目前有很多的莊稼。你覺得對什麼工作格外愛好?』
『就是神父願意指示給我的那份工作。』
『現在有三種職務:在亞斯底的步底利辣當副本堂,或在培養院這裡做倫理神學講師,或在濟良所附近那所小醫院裡當院長。你選擇哪一種?』
『選擇神父你認為適合的那一種。』
『你不對某一件事比對其他的事更感興趣嗎?』
『我的興趣是從事教育青年的工作。神父你儘管隨意安排我。我把神父你的主意,看作天主的聖意。』
『你現在心裡轉些什麼念頭?明悟裡想些什麼?』
『現在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許多求我援助的兒童們中間。』
『那麼你去度一個星期的假。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要去什麼地方工作。』
過了假期以後,賈發束神父又讓我過了一個多星期,卻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問他一句話。
過了假期以後,賈發束神父又讓我過了一個多星期,卻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問他一句話。
『因為我承認神父你所作的決定,就是天主的聖意;我不願意加入一些我自己的意見。』
『你收拾行李,到神學博士包萊那裡去。你在那裡,將擔任聖斐落美娜那座小醫院的院長。此外,你也要在濟良所裡工作。同時天主將會把你要為青年們做的工作,交託在你手中的。』(《母院史》126-127) 『一天,賈發束神父叫我去見他,對我說:『現在你已畢業,應該出去工作了。目前有很多的莊稼。你覺得對什麼工作格外愛好?』
『就是神父願意指示給我的那份工作。』
『現在有三種職務:在亞斯底的步底利辣當副本堂,或在培養院這裡做倫理神學講師,或在濟良所附近那所小醫院裡當院長。你選擇哪一種?』
『選擇神父你認為適合的那一種。』
『你不對某一件事比對其他的事更感興趣嗎?』
『我的興趣是從事教育青年的工作。神父你儘管隨意安排我。我把神父你的主意,看作天主的聖意。』
『你現在心裡轉些什麼念頭?明悟裡想些什麼?』
『現在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許多求我援助的兒童們中間。』
『那麼你去度一個星期的假。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要去什麼地方工作。』
過了假期以後,賈發束神父又讓我過了一個多星期,卻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問他一句話。
過了假期以後,賈發束神父又讓我過了一個多星期,卻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問他一句話。
『因為我承認神父你所作的決定,就是天主的聖意;我不願意加入一些我自己的意見。』
『你收拾行李,到神學博士包萊那裡去。你在那裡,將擔任聖斐落美娜那座小醫院的院長。此外,你也要在濟良所裡工作。同時天主將會把你要為青年們做的工作,交託在你手中的。』(《母院史》12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