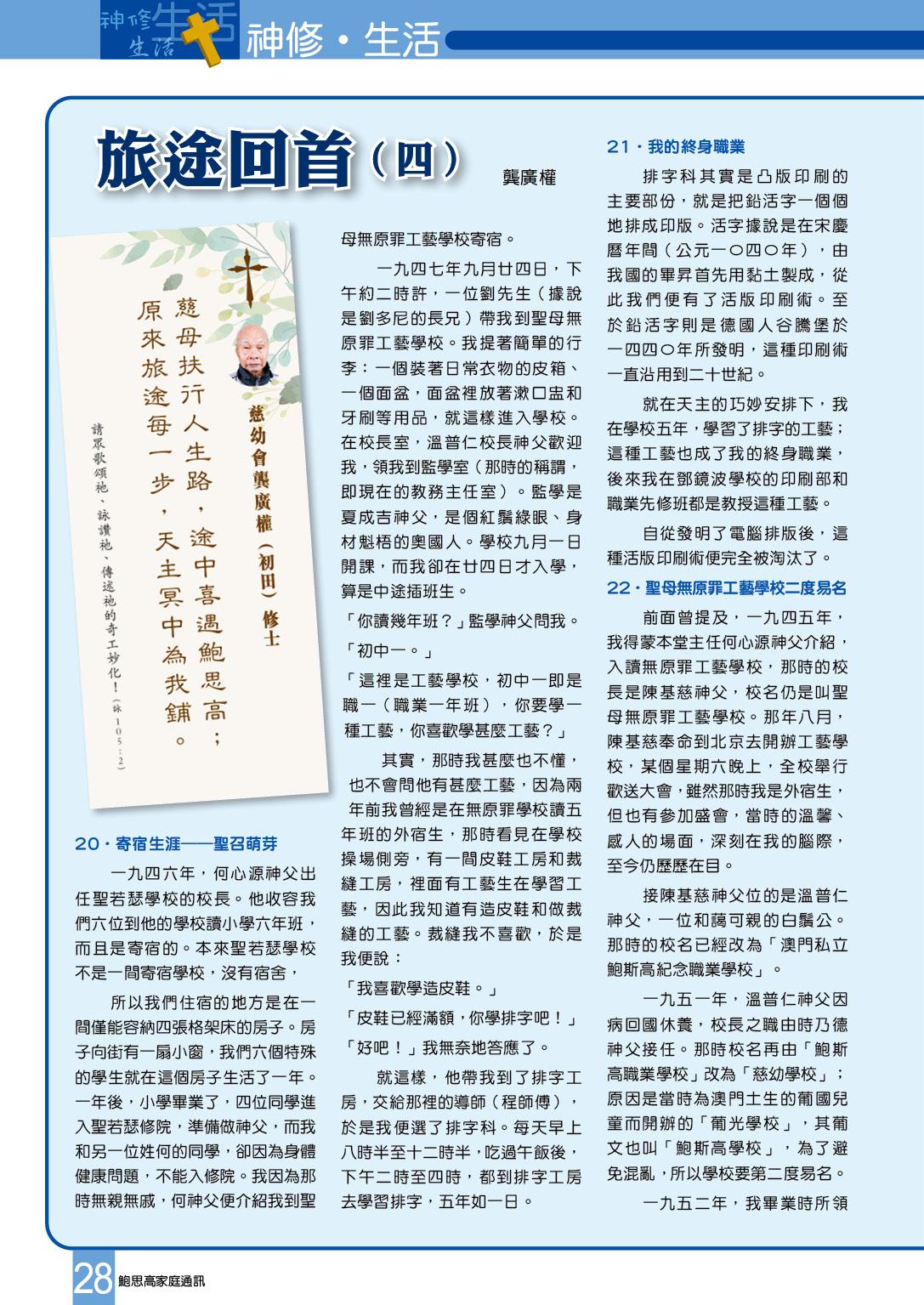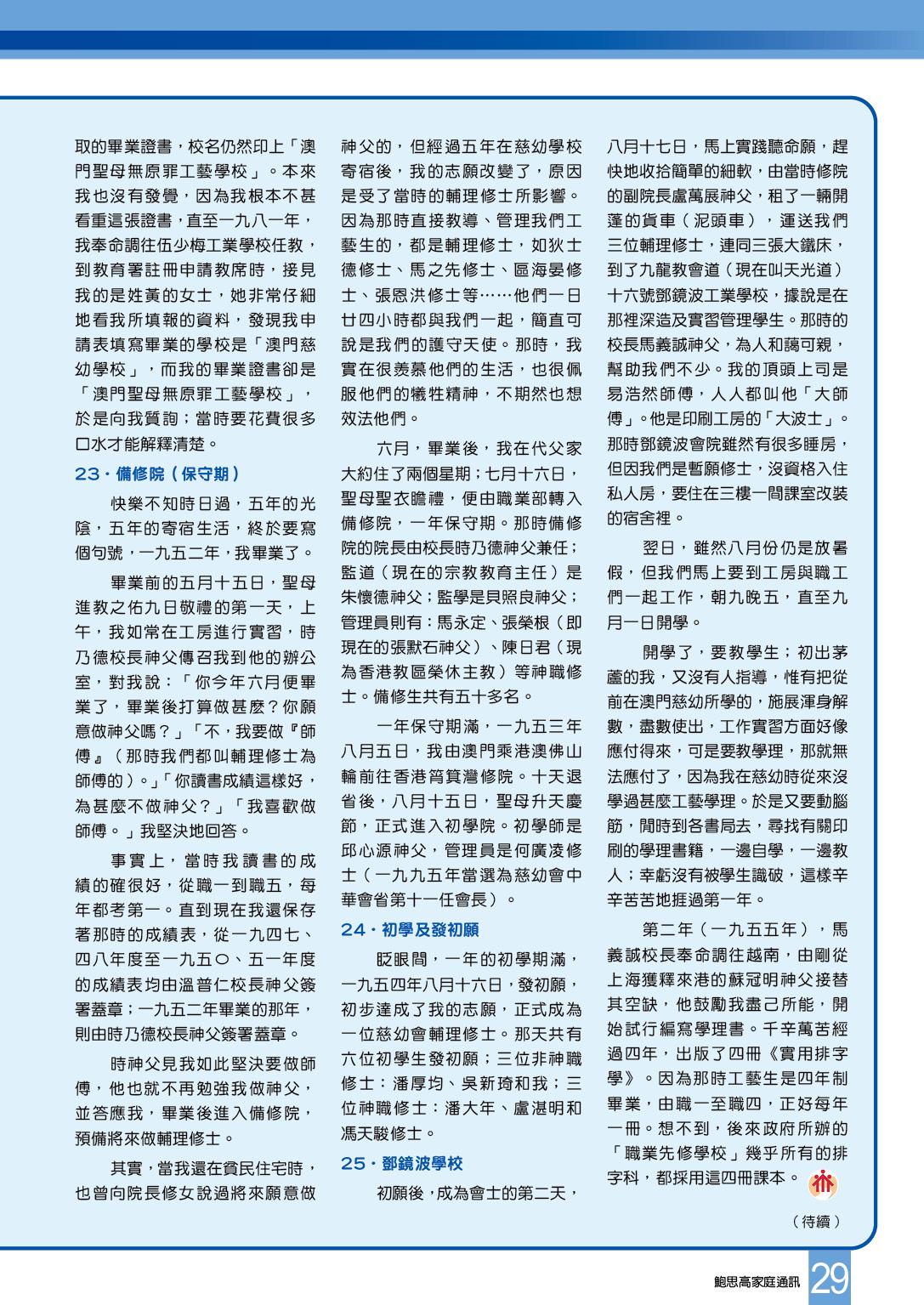旅途回首(四)
龔廣權
- 寄宿生涯——聖召萌芽
一九四六年,何心源神父出任聖若瑟學校的校長。他收容我們六位到他的學校讀小學六年班,而且是寄宿的。本來聖若瑟學校不是一間寄宿學校,沒有宿舍,
所以我們住宿的地方是在一間僅能容納四張格架床的房子。房子向街有一扇小窗,我們六個特殊的學生就在這個房子生活了一年。一年後,小學畢業了,四位同學進入聖若瑟修院,準備做神父,而我和另一位姓何的,卻因為身體健康問題,不能入修院。我因為那時無親無戚,何神父便介紹我到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寄宿。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四日,下午約二時許,一位劉先生(據說是劉多尼的長兄)帶我到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我提著簡單的行李:一個裝著日常衣物的皮箱、一個面盆,面盆裡放著漱口盅和牙刷等用品,就這樣進入學校。在校長室,溫普仁校長神父歡迎我,領我到監學室(那時的稱謂,即現在的教務主任室)。監學是夏成吉神父,是個紅鬚綠眼、身材魁梧的奧國人。學校九月一日開課,而我卻在廿四日才入學,算是中途插班生。
「你讀幾年班?」監學神父問我。
「初中一。」
「這裡是工藝學校,初中一即是職一(職業一年班),你要學一種工藝,你喜歡學甚麼工藝?」
其實,那時我甚麼也不懂,也不會問他有甚麼工藝,因為兩年前我曾經是在無原罪學校讀五年班的外宿生,那時看見在學校操場側旁,有一間皮鞋工房和裁縫工房,裡面有工藝生在學習工藝,因此我知道有造皮鞋和做裁縫的工藝。裁縫我不喜歡,於是我便說:
「我喜歡學造皮鞋。」
「皮鞋已經滿額,你學排字吧!」
「好吧!」我無奈地答應了。
就這樣,他帶我到了排字工房,交給那裡的導師(程師傅),於是我便選了排字科。每天早上八時半至十二時半,吃過午飯後,下午二時至四時,都到排字工房去學習排字,五年如一日。
- 我的終身職業
排字科其實是凸版印刷的主要部份,就是把鉛活字一個個地排成印版。活字據說是在宋慶曆年間(公元一〇四〇年),由我國的畢昇首先用黏土製成,從此我們便有了活版印刷術。至於鉛活字則是德國人谷騰堡於一四四〇年所發明,這種印刷術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
就在天主的巧妙安排下,我在學校五年,學習了排字的工藝;這種工藝也成了我的終身職業,後來我在鄧鏡波學校的印刷部和職業先修班都是教授這種工藝。
自從發明了電腦排版後,這種活版印刷術便完全被淘汰了。
- 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二度易名
前面曾提及,一九四五年,我得蒙本堂主任何心源神父介紹,入讀無原罪工藝學校,那時的校長是陳基慈神父,校名仍是叫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那年八月,陳基慈奉命到北京去開辦工藝學校,某個星期六晚上,全校舉行歡送大會,雖然那時我是外宿生,但也有參加盛會,當時的溫馨、感人的場面,深刻在我的腦際,至今仍歷歷在目。
接陳基慈神父位的是溫普仁神父,一位和藹可親的白鬚公。那時的校名已經改為「澳門私立鮑斯高紀念職業學校」。
一九五一年,溫普仁神父因病回國休養,校長之職由時乃德神父接任。那時校名再由「鮑斯高職業學校」改為「慈幼學校」;原因是當時為澳門土生的葡國兒童而開辦的「葡光學校」,其葡文也叫「鮑斯高學校」,為了避免混亂,所以學校要第二度易名。
一九五二年,我畢業時所領取的畢業證書,校名仍然印上「澳門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本來我也沒有發覺,因為我根本不甚看重這張證書,直至一九八一年,我奉命調往伍少梅工業學校任教,到教育署註冊申請教席時,接見我的是姓黃的女士,她非常仔細地看我所填報的資料,發現我申請表填寫畢業的學校是「澳門慈幼學校」,而我的畢業證書卻是「澳門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於是向我質詢;當時要花費很多口水才能解釋清楚。
23.備修院(保守期)
快樂不知時日過,五年的光陰,五年的寄宿生活,終於要寫個句號,一九五二年,我畢業了。
畢業前的五月十五日,聖母進教之佑九日敬禮的第一天,上午,我如常在工房進行實習,時乃德校長神父傳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
「你今年六月便畢業了,畢業後打算做甚麽?你願意做神父嗎?」「不,我要做『師傅』(那時我們都叫輔理修士為師傅的)。」「你讀書成績這樣好,為甚麼不做神父?」「我喜歡做師傅。」我堅決地回答。
事實上,當時我讀書的成績的確很好,從職一到職五,每年都考第一。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那時的成績表,從一九四七、四八年度至一九五〇、五一年度的成績表均由溫普仁校長神父簽署蓋章;一九五二年畢業的那年,則由時乃德校長神父簽署蓋章。
時神父見我如此堅決要做師傅,他也就不再勉強我做神父,並答應我,畢業後進入備修院,預備將來做輔理修士。
其實,當我還在貧民住宅時,也曾向院長修女說過將來願意做神父的,但經過五年在慈幼學校寄宿後,我的志願改變了,原因是受了當時的輔理修士所影響。因為那時直接教導、管理我們工藝生的,都是輔理修士,如狄士德修士、馬之先修士、區海晏修士、張恩洪修士等……他們一日廿四小時都與我們一起,簡直可說是我們的護守天使。那時,我實在很羨慕他們的生活,也很佩服他們的犧牲精神,不期然也想效法他們。
六月,畢業後,我在代父家大約住了兩個星期;七月十六日,聖母聖衣瞻禮,便由職業部轉入備修院,一年保守期。那時備修院的院長由校長時乃德神父兼任;監道(現在的宗教教育主任)是朱懷德神父;監學是貝照良神父;管理員則有:馬永定、張榮根(即現在的張默石神父)、陳日君(現為香港教區榮休主教)等神職修士。備修生共有五十多名。
一年保守期滿,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我由澳門乘港澳佛山輪前往香港筲箕灣修院。十天退省後,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慶節,正式進入初學院。初學師是邱心源神父,管理員是何廣凌修士(一九九五年當選為慈幼會中華會省第十一任會長)。
24.初學及發初願
眨眼間,一年的初學期滿,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發初願,初步達成了我的志願,正式成為一位慈幼會輔理修士。那天共有六位初學生發初願;三位非神職修士:潘厚均、吳新琦和我;三位神職修士:潘大年、盧湛明和馮天駿修士。
- 鄧鏡波學校
初願後,成為會士的第二天,八月十七日,馬上實踐聽命願,趕快地收拾簡單的細軟,由當時修院的副院長盧萬展神父,租了一輛開蓬的貨車(泥頭車),運送我們三位輔理修士,連同三張大鐵床,到了九龍教會道(現在叫天光道)十六號鄧鏡波工業學校,據說是在那裡深造及實習管理學生。那時的校長馬義誠神父,為人和藹可親,幫助我們不少。我的頂頭上司是易浩然師傅,人人都叫他「大師傅」。他是印刷工房的「大波士」。那時鄧鏡波會院雖然有很多睡房,但因我們是暫願修士,沒資格入住私人房,要住在三樓一間課室改裝的宿舍裡。
翌日,雖然八月份仍是放暑假,但我們馬上要到工房與職工們一起工作,朝九晚五,直至九月一日開學。
開學了,要教學生;初出茅蘆的我,又沒有人指導,惟有把從前在澳門慈幼所學的,施展渾身解數,盡數使出,工作實習方面好像應付得來,可是要教學理,那就無法應付了,因為我在慈幼時從來沒學過甚麼工藝學理。於是又要動腦筋,閒時到各書局去,尋找有關印刷的學理書籍,一邊自學,一邊教人;幸虧沒有被學生識破,這樣辛辛苦苦地捱過第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五年),馬義誠校長奉命調往越南,由剛從上海獲釋來港的蘇冠明神父接替其空缺,他鼓勵我盡己所能,開始試行編寫學理書。千辛萬苦經過四年,出版了四冊《實用排字學》。因為那時工藝生是四年制畢業,由職一至職四,正好每年一冊。想不到,後來政府所辦的「職業先修學校」幾乎所有的排字科,都採用這四冊課本。(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