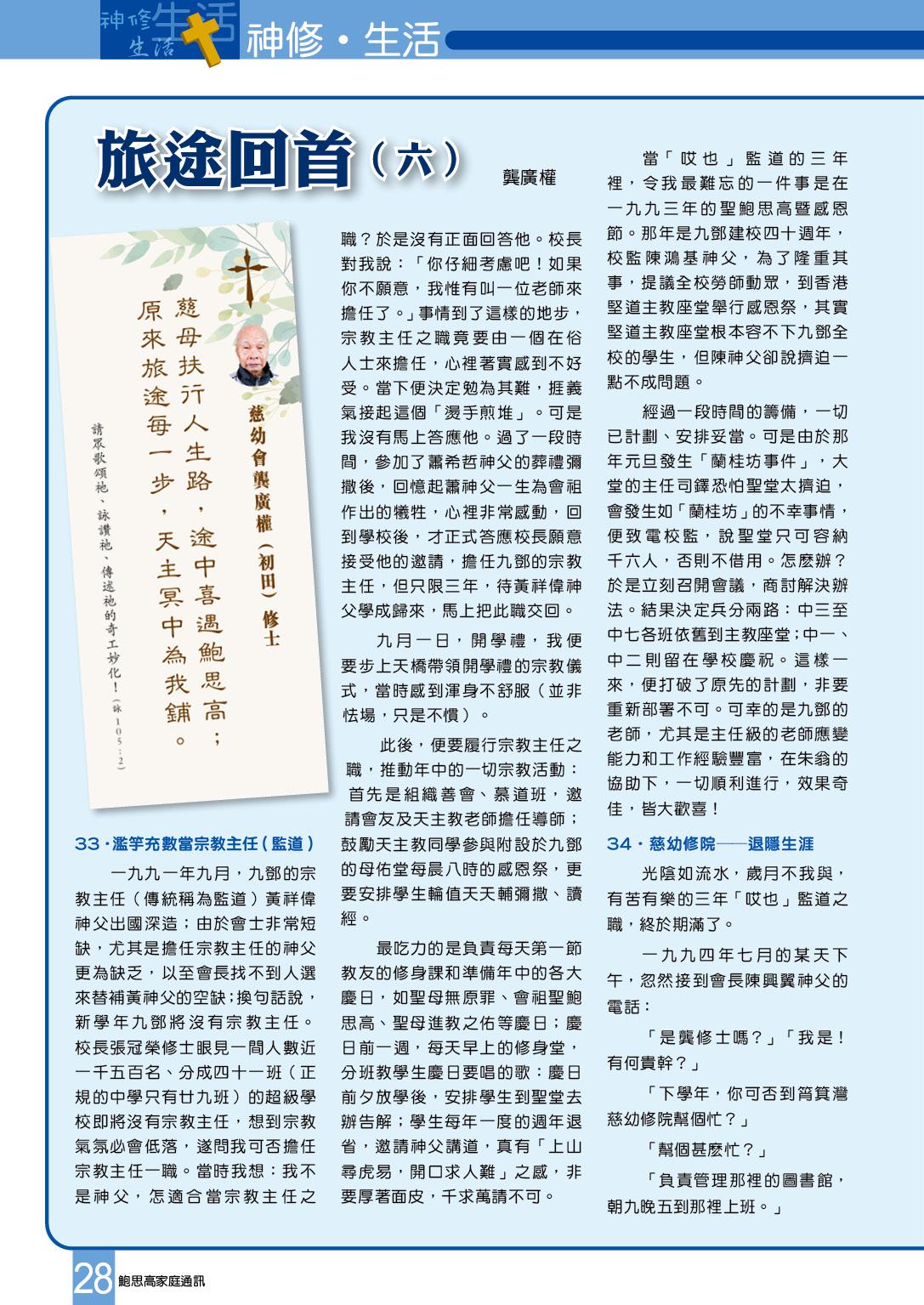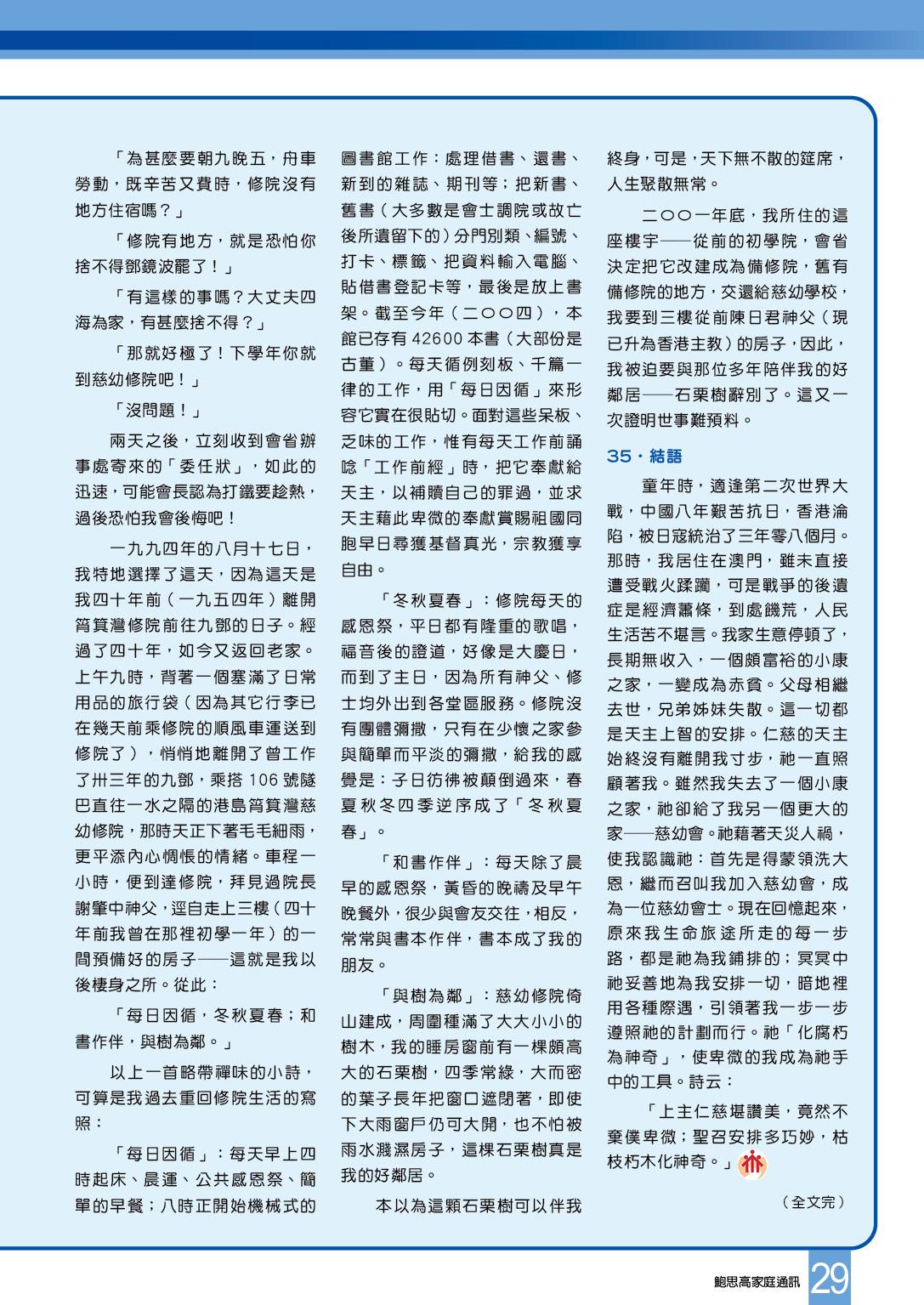旅途回首(六)
龔廣權
- 濫竽充數當宗教主任(監道)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鄧的宗教主任(傳統稱為監道)黃祥偉神父出國深造;由於會士非常短缺,尤其是擔任宗教主任的神父更為缺乏,以至會長找不到人選來替補黃神父的空缺;換句話說,新學年九鄧將沒有宗教主任。校長張冠榮修士眼見一間人數近一千五百名、分成四十一班(正規的中學只有廿九班)的超級學校即將沒有宗教主任,想到宗教氣氛必會低落,遂問我可否擔任宗教主任一職。當時我想:我不是神父,怎適合當宗教主任之職?於是沒有正面回答他。校長對我說:「你仔細考慮吧!如果你不願意,我惟有叫一位老師來擔任了。」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宗教主任之職竟要由一個在俗人士來擔任,心裡著實感到不好受。當下便決定勉為其難,捱義氣接起這個「燙手煎堆」。可是我沒有馬上答應他。過了一段時間,參加了蕭希哲神父的葬禮彌撒後,回憶起蕭神父一生為會祖作出的犧牲,心裡非常感動,回到學校後,才正式答應校長願意接受他的邀請,擔任九鄧的宗教主任,但只限三年,待黃祥偉神父學成歸來,馬上把此職交回。
九月一日,開學禮,我便要步上天橋帶領開學禮的宗教儀式,當時感到渾身不舒服(並非怯場,只是不慣)。
此後,便要履行宗教主任之職,推動年中的一切宗教活動:首先是組織善會、慕道班,邀請會友及天主教老師擔任導師;鼓勵天主教同學參與附設於九鄧的母佑堂每晨八時的感恩祭,更要安排學生輪值天天輔彌撒、讀經。
最吃力的是負責每天第一節教友的修身課和準備年中的各大慶日,如聖母無原罪、會祖聖鮑思高、聖母進教之佑等慶日;慶日前一週,每天早上的修身堂,分班教學生慶日要唱的歌:慶日前夕放學後,安排學生到聖堂去辦告解;學生每年一度的週年退省,邀請神父講道,真有「上山尋虎易,開口求人難」之感,非要厚著面皮,千求萬請不可。
當「哎也」監道的三年裡,令我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在一九九三年的聖鮑思高暨感恩節。那年是九鄧建校四十週年,校監陳鴻基神父,為了隆重其事,提議全校勞師動眾,到香港堅道主教座堂舉行感恩祭,其實堅道主教座堂根本容不下九鄧全校的學生,但陳神父卻說擠迫一點不成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一切已計劃、安排妥當。可是由於那年元旦發生「蘭桂坊事件」,大堂的主任司鐸恐怕聖堂太擠迫,會發生如「蘭桂坊」的不幸事情,便致電校監,說聖堂只可容納千六人,否則不借用。怎麽辦?於是立刻召開會議,商討解決辦法。結果決定兵分兩路:中三至中七各班依舊到主教座堂;中一、中二則留在學校慶祝。這樣一來,便打破了原先的計劃,非要重新部署不可。可幸的是九鄧的老師,尤其是主任級的老師應變能力和工作經驗豐富,在朱翁的協助下,一切順利進行,效果奇佳,皆大歡喜!
- 慈幼修院──退隱生涯
光陰如流水,歲月不我與,有苦有樂的三年「哎也」監道之職,終於期滿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的某天下午,忽然接到會長陳興翼神父的電話:
「是龔修士嗎?」「我是!有何貴幹?」
「下學年,你可否到筲箕灣慈幼修院幫個忙?」
「幫個甚甚麽忙?」
「負責管理那裡的圖書館,朝九晚五到那裡上班。」
「為甚甚麼要朝九晚五,舟車勞動,既辛苦又費時,修院沒有地方住宿嗎?」
「修院有地方,就是恐怕你捨不得鄧鏡波罷了!」
「有這樣的事嗎?大丈夫四海為家,有甚麼捨不得?」
「那就好極了!下學年你就到慈幼修院吧!」
「沒問題!」
兩天之後,立刻收到會省辦事處寄來的「委任狀」,如此的迅速,可能會長認為打鐵要趁熱,過後恐怕我會後悔吧!
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七日,我特地選擇了這天,因為這天是我四十年前(一九五四年)離開筲箕灣修院前往九鄧的日子。經過了四十年,如今又返回老家。上午九時,背著一個塞滿了日常用品的旅行袋(因為其它行李已在幾天前乘修院的順風車運送到修院了),悄悄地離開了曾工作了卅三年的九鄧,乘搭106號隧巴直往一水之隔的港島筲箕灣慈幼修院,那時天正下著毛毛細雨,更平添內心惆悵的情緒。車程一小時,便到達修院,拜見過院長謝肇中神父,逕自走上三樓(四十年前我曾在那裡初學一年)的一間預備好的房子——這就是我以後棲身之所。從此:
「每日因循,冬秋夏春;和書作伴,與樹為鄰。」
以上一首略帶禪味的小詩,可算是我過去重回修院生活的寫照:
「每日因循」:每天早上四時起床、晨運、公共感恩祭、簡單的早餐;八時正開始機械式的圖書館工作:處理借書、還書、新到的雜誌、期刊等;把新書、舊書(大多數是會士調院或故亡後所遺留下的)分門別類、編號、打卡、標籤、把資料輸入電腦、貼借書登記卡等,最後是放上書架。截至今年(二〇〇四),本館已存有42600本書(大部份是古董)。每天循例刻板、千篇一律的工作,用「每日因循」來形容它實在很貼切。面對這些呆板、乏味的工作,惟有每天工作前誦唸「工作前經」時,把它奉獻給天主,以補贖自己的罪過,並求天主藉此卑微的奉獻賞賜祖國同胞早日尋獲基督真光,宗教獲享自由。
「冬秋夏春」:修院每天的感恩祭,平日都有隆重的歌唱,福音後的證道,好像是大慶日,而到了主日,因為所有神父、修士均外出到各堂區服務。修院沒有團體彌撒,只有在少懷之家參與簡單而平淡的彌撒,給我的感覺是:子日彷彿被顛倒過來,春夏秋冬四季逆序成了「冬秋夏春」。
「和書作伴」:每天除了晨早的感恩祭,黃昏的晚禱及早午晚餐外,很少與會友交往,相反,常常與書本作伴,書本成了我的朋友。
「與樹為鄰」:慈幼修院倚山建成,周圍種滿了大大小小的樹木,我的睡房窗前有一棵頗高大的石栗樹,四季常綠,大而密的葉子長年把窗口遮閉著,即使下大雨窗戶仍可大開,也不怕被雨水濺濕房子,這棵石栗樹真是我的好鄰居。
本以為這顆石栗樹可以伴我終身,可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人生聚散無常。
二〇〇一年底,我所住的這座樓宇——從前的初學院,會省決定把它改建成為備修院,舊有備修院的地方,交還給慈幼學校,我要到三樓從前陳日君神父(現已升為香港主教)的房子,因此,我被迫要與那位多年陪伴我的好鄰居——石栗樹辭別了。這又一次證明世事難預料。
- 結語
童年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八年艱苦抗日,香港淪陷,被日寇統治了三年零八個月。那時,我居住在澳門,雖未直接遭受戰火蹂躪,可是戰爭的後遺症是經濟蕭條,到處饑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我家生意停頓了,長期無收入,一個頗富裕的小康之家,一變成為赤貧。父母相繼去世,兄弟姊妹失散。這一切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仁慈的天主始終沒有離開我寸步,祂一直照顧著我。雖然我失去了一個小康之家,祂卻給了我另一個更大的家——慈幼會。祂藉著天災人禍,使我認識祂:首先是得蒙領洗大恩,繼而召叫我加入慈幼會,成為一位慈幼會士。現在回憶起來,原來我生命旅途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祂為我鋪排的;冥冥中祂妥善地為我安排一切,暗地裡用各種際遇,引領著我一步一步遵照祂的計劃而行。祂「化腐朽為神奇」,使卑微的我成為祂手中的工具。詩云:
「上主仁慈堪讚美,竟然不棄僕卑微;聖召安排多巧妙,枯枝朽木化神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