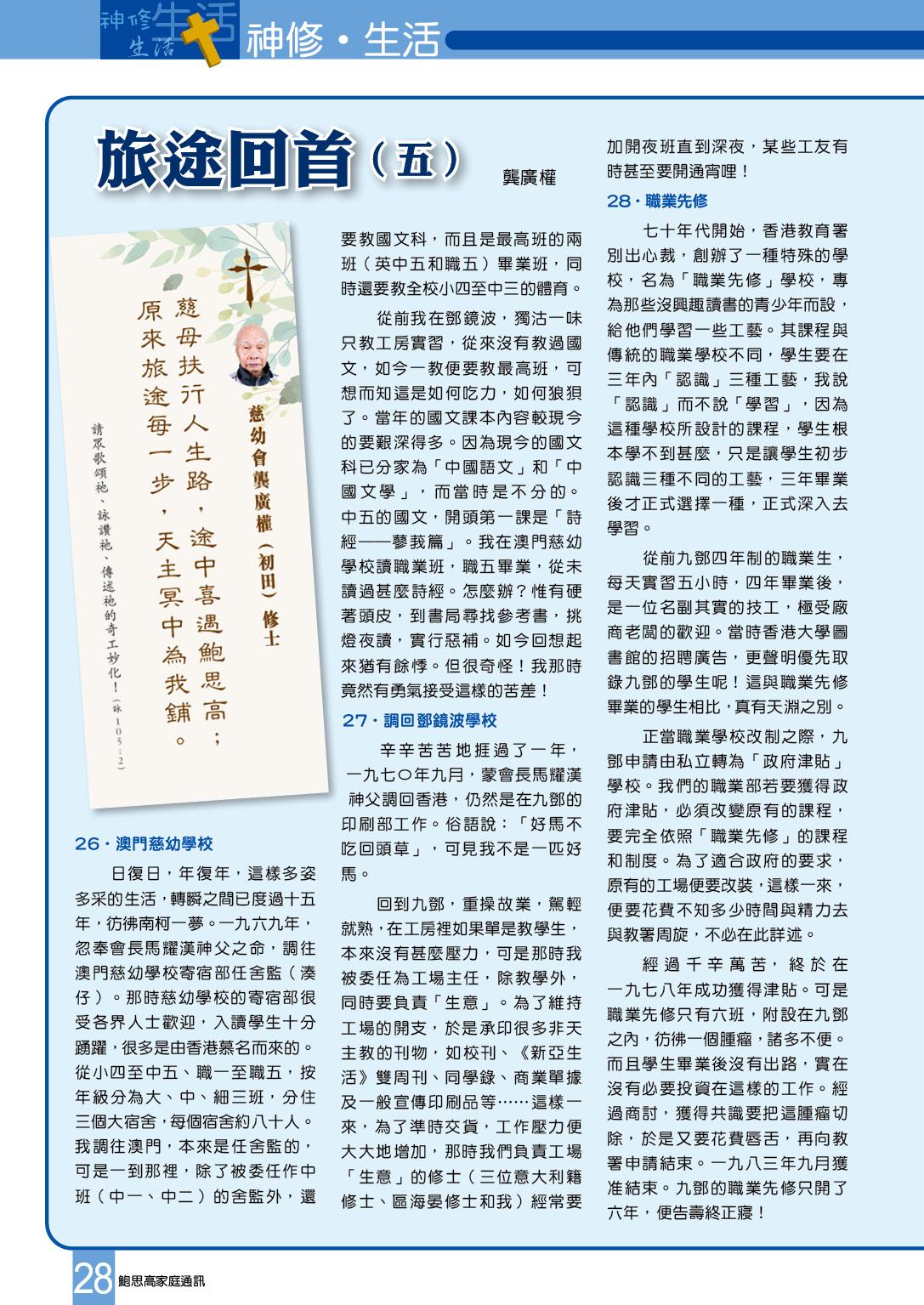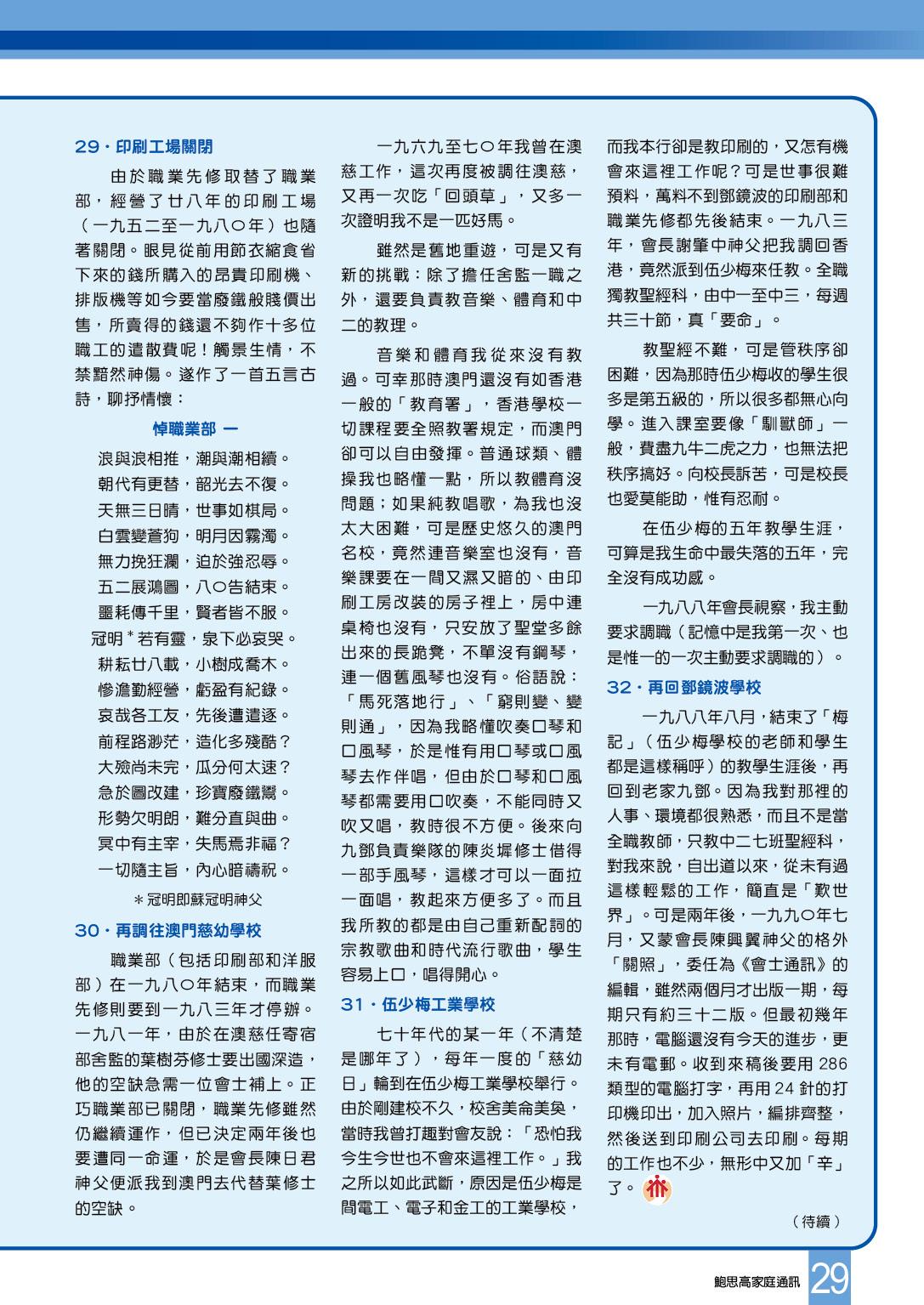旅途回首(五)
龔廣權
- 澳門慈幼學校
日復日,年復年,這樣多姿多采的生活,轉瞬之間已度過十五年,彷彿南柯一夢。一九六九年,忽奉會長馬耀漢神父之命,調往澳門慈幼學校寄宿部任舍監(湊仔)。那時慈幼學校的寄宿部很受各界人士歡迎,入讀學生十分踴躍,很多是由香港慕名而來的。從小四至中五、職一至職五,按年級分為大、中、細三班,分住三個大宿舍,每個宿舍約八十人。我調往澳門,本來是任舍監的,可是一到那裡,除了被委任作中班(中一、中二)的舍監外,還要教國文科,而且是最高班的兩班(英中五和職五)畢業班,同時還要教全校小四至中三的體育。
從前我在鄧鏡波,獨沽一味只教工房實習,從來沒有教過國文,如今一教便要教最高班,可想而知這是如何吃力,如何狼狽了。當年的國文課本內容較現今的要艱深得多。因為現今的國文科已分家為「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而當時是不分的。中五的國文,開頭第一課是「詩經——蓼莪篇」。我在澳門慈幼學校讀職業班,職五畢業,從未讀過甚麼詩經。怎麼辦?惟有硬著頭皮,到書局尋找參考書,挑燈夜讀,實行惡補。如今回想起來猶有餘悸。但很奇怪!我那時竟然有勇氣接受這樣的苦差!
- 調回鄧鏡波學校
辛辛苦苦地捱過了一年,一九七〇年九月,蒙會長馬耀漢神父調回香港,仍然是在九鄧的印刷部工作。俗語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可見我不是一匹好馬。
回到九鄧,重操故業,駕輕就熟,在工房裡如果單是教學生,本來沒有甚麼壓力,可是那時我被委任為工場主任,除教學外,同時要負責「生意」。為了維持工場的開支,於是承印很多非天主教的刊物,如校刊、《新亞生活》雙周刊、同學錄、商業單據及一般宣傳印刷品等⋯⋯這樣一來,為了準時交貨,工作壓力便大大地增加,那時我們負責工場「生意」的修士(三位意大利籍修士、區海晏修士和我)經常要加開夜班直到深夜,某些工友有時甚至要開通宵哩!
- 職業先修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教育署別出心裁,創辦了一種特殊的學校,名為「職業先修」學校,專為那些沒興趣讀書的青少年而設,給他們學習一些工藝。其課程與傳統的職業學校不同,學生要在三年內「認識」三種工藝,我說「認識」而不說「學習」,因為這種學校所設計的課程,學生根本學不到甚麼,只是讓學生初步認識三種不同的工藝,三年畢業後才正式選擇一種,正式深入去學習。
從前九鄧四年制的職業生,每天實習五小時,四年畢業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技工,極受廠商老闆的歡迎。當時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招聘廣告,更聲明優先取錄九鄧的學生呢!這與職業先修畢業的學生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正當職業學校改制之際,九鄧申請由私立轉為「政府津貼」學校。我們的職業部若要獲得政府津貼,必須改變原有的課程,要完全依照「職業先修」的課程和制度。為了適合政府的要求,原有的工場便要改裝,這樣一來,便要花費不知多少時間與精力去與教署周旋,不必在此詳述。
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一九七八年成功獲得津貼。可是職業先修只有六班,附設在九鄧之內,彷彿一個腫瘤,諸多不便。而且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實在沒有必要投資在這樣的工作。經過商討,獲得共識要把這腫瘤切除,於是又要花費唇舌,再向教署申請結束。一九八三年九月獲准結束。九鄧的職業先修只開了六年,便告壽終正寢!
29.印刷工場關閉
由於職業先修取替了職業部,經營了廿八年的印刷工場(一九五二至一九八〇年)也隨著關閉。眼見從前用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所購入的昂貴印刷機、排版機等如今要當廢鐵般賤價出售,所賣得的錢還不夠作十多位職工的遣散費呢!觸景生情,不禁黯然神傷。遂作了一首五言古詩,聊抒情懷:
悼職業部 一
浪與浪相推,潮與潮相續。
朝代有更替,韶光去不復。
天無三日晴,世事如棋局。
白雲變蒼狗,明月因霧濁。
無力挽狂瀾,迫於強忍辱。
五二展鴻圖,八〇告結束。
噩耗傳千里,賢者皆不服。
冠明若有靈,泉下必哀哭。(註)
耕耘廿八載,小樹成喬木。
慘澹勤經營,虧盈有紀錄。
哀哉各工友,先後遭遣逐。
前程路渺茫,造化多殘酷?
大殮尚未完,瓜分何太速?
急於圖改建,珍寶廢鐵鬻。
形勢欠明朗,難分直與曲。
冥中有主宰,失馬焉非福?
一切隨主旨,內心暗禱祝。
(註)冠明即蘇冠明神父
- 再調往澳門慈幼學校
職業部(包括印刷部和洋服部)在一九八〇年結束,而職業先修則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停辦。一九八一年,由於在澳慈任寄宿部舍監的葉樹芬修士要出國深造,他的空缺急需一位會士補上。正巧職業部已關閉,職業先修雖然仍繼續運作,但已決定兩年後也要遭同一命運,於是會長陳日君神父便派我到澳門去代替葉修士的空缺。
一九六九至七〇年我曾在澳慈工作,這次再度被調往澳慈,又再一次吃「回頭草」,又多一次證明我不是一匹好馬。
雖然是舊地重遊,可是又有新的挑戰:除了擔任舍監一職之外,還要負責教音樂、體育和中二的教理。
音樂和體育我從來沒有教過。可幸那時澳門還沒有如香港一般的「教育署」,香港學校一切課程要全照教署規定,而澳門卻可以自由發揮。普通球類、體操我也略懂一點,所以教體育沒問題;如果純教唱歌,為我也沒太大困難,可是歷史悠久的澳門名校,竟然連音樂室也沒有,音樂課要在一間又濕又暗的、由印刷工房改裝的房子裡上,房中連桌椅也沒有,只安放了聖堂多餘出來的長跪凳,不單沒有鋼琴,連一個舊風琴也沒有。俗語說:「馬死落地行」、「窮則變、變則通」,因為我略懂吹奏口琴和口風琴,於是惟有用口琴或口風琴去作伴唱,但由於口琴和口風琴都需要用口吹奏,不能同時又吹又唱,教時很不方便。後來向九鄧負責樂隊的陳炎墀修士借得一部手風琴,這樣才可以一面拉一面唱,教起來方便多了。而且我所教的都是由自己重新配詞的宗教歌曲和時代流行歌曲,學生容易上口,唱得開心。
- 伍少梅工業學校
七十年代的某一年(不清楚是哪年了),每年一度的「慈幼日」輪到在伍少梅工業學校舉行。由於剛建校不久,校舍美侖美奐,當時我曾打趣對會友說:「恐怕我今生今世也不會來這裡工作。」我之所以如此武斷,原因是伍少梅是間電工、電子和金工的工業學校,而我本行卻是教印刷的,又怎有機會來這裡工作呢?可是世事很難預料,萬料不到鄧鏡波的印刷部和職業先修都先後結束。一九八三年,會長謝肇中神父把我調回香港,竟然派到伍少梅來任教。全職獨教聖經科,由中一至中三,每週共三十節,真「要命」。
教聖經不難,可是管秩序卻困難,因為那時伍少梅收的學生很多是第五級的,所以很多都無心向學。進入課室要像「馴獸師」一般,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把秩序搞好。向校長訴苦,可是校長也愛莫能助,惟有忍耐。
在伍少梅的五年教學生涯,可算是我生命中最失落的五年,完全沒有成功感。
一九八八年會長視察,我主動要求調職(記憶中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動要求調職的)。
- 再回鄧鏡波學校
一九八八年八月,結束了「梅記」(伍少梅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是這樣稱呼)的教學生涯後,再回到老家九鄧。因為我對那裡的人事、環境都很熟悉,而且不是當全職教師,只教中二七班聖經科,對我來說,自出道以來,從未有過這樣輕鬆的工作,簡直是「歎世界」。可是兩年後,一九九〇年七月,又蒙會長陳興翼神父的格外「關照」,委任為《會士通訊》的編輯,雖然兩個月才出版一期,每期只有約三十二版。但最初幾年那時,電腦還沒有今天的進步,更未有電郵。收到來稿後要用286類型的電腦打字,再用24針的打印機印出,加入照片,編排齊整,然後送到印刷公司去印刷。每期的工作也不少,無形中又加「辛」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