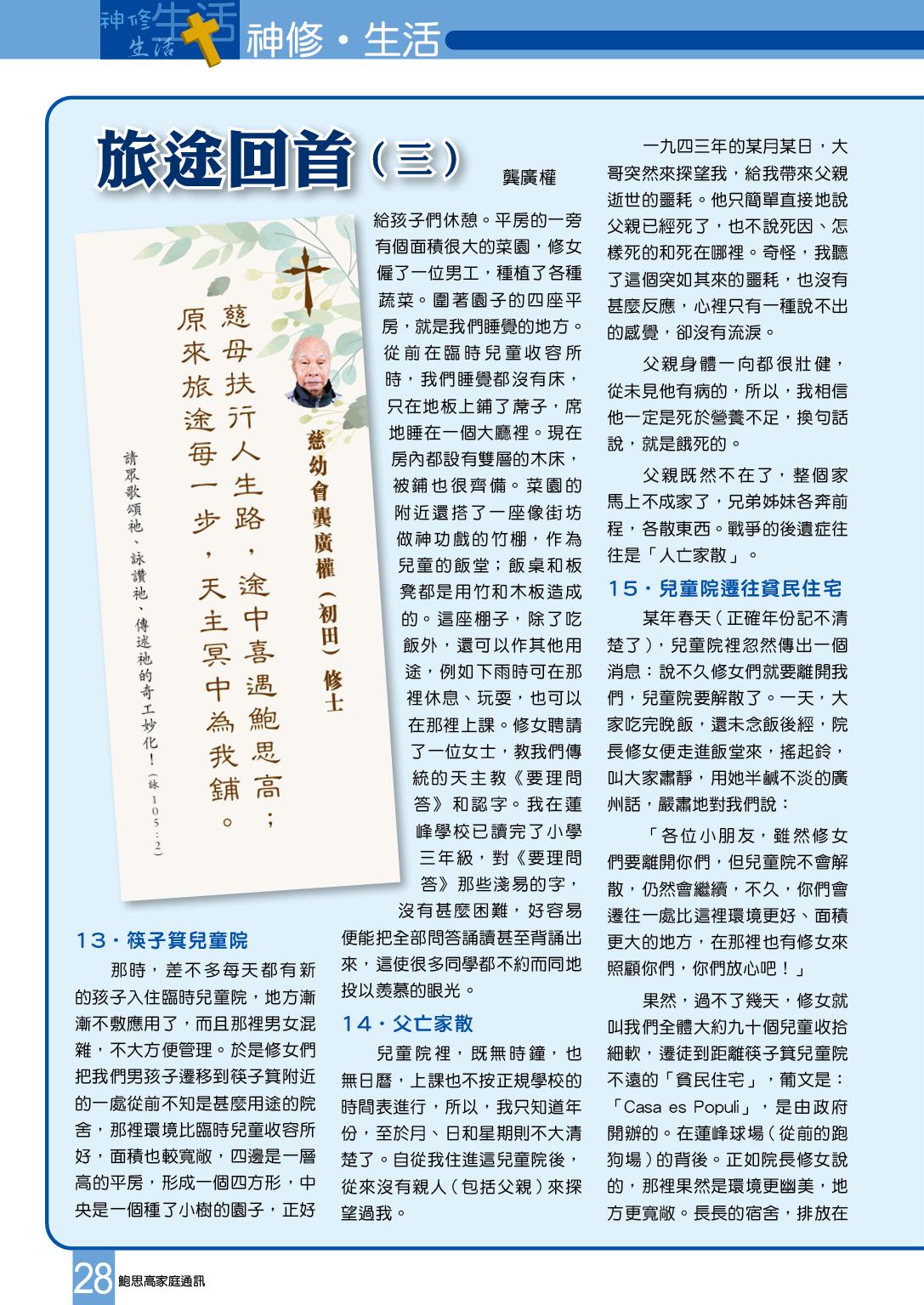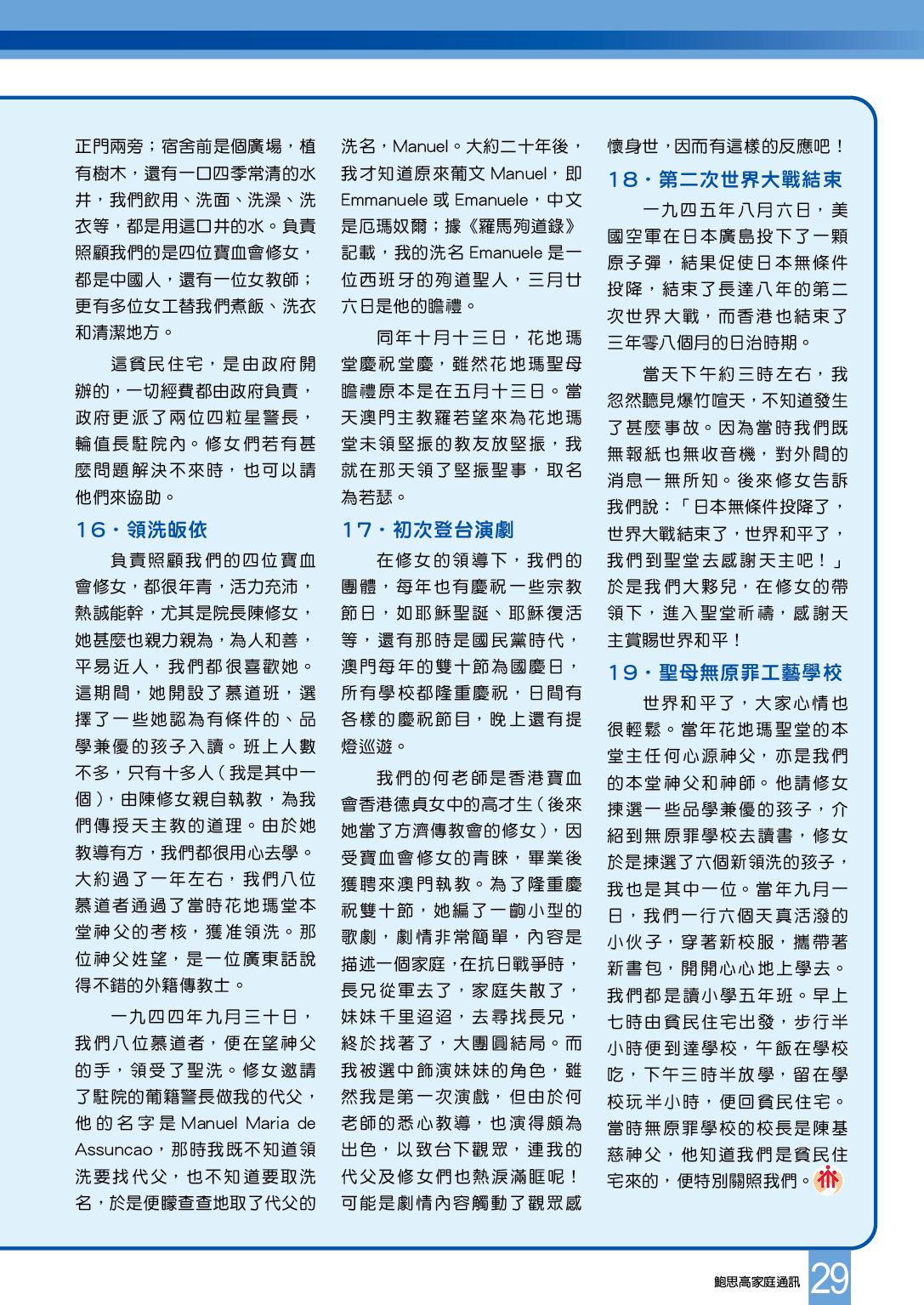旅途回首(三)
龔廣權
- 筷子箕兒童院
那時,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孩子入住臨時兒童院,地方漸漸不敷應用了,而且那裡男女混雜,不大方便管理。於是修女們把我們男孩子遷移到筷子箕附近的一處從前不知是甚麼用途的院舍,那裡環境比臨時兒童收容所好,面積也較寬敞,四邊是一層高的平房,形成一個四方形,中央是一個種了小樹的園子,正好給孩子們休憩。平房的一旁有個面積很大的菜園,修女僱了一位男工,種植了各種蔬菜。圍著園子的四座平房,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從前在臨時兒童收容所時,我們睡覺都沒有床,只在地板上鋪了蓆子,席地睡在一個大廳裡。現在房內都設有雙層的木床,被鋪也很齊備。菜園的附近還搭了一座像街坊做神功戲的竹棚,作為兒童的飯堂;飯桌和板凳都是用竹和木板造成的。這座棚子,除了吃飯外,還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下雨時可在那裡休息、玩耍,也可以在那裡上課。修女聘請了一位女士,教我們傳統的天主教《要理問答》和認字。我在蓮峰學校已讀完了小學三年級,對《要理問答》那些淺易的字,沒有甚麼困難,好容易便能把全部問答誦讀甚至背誦出來,這使很多同學都不約而同地投以羨慕的眼光。
- 父亡家散
兒童院裡,既無時鐘,也無日曆,上課也不按正規學校的時間表進行,所以,我只知道年份,至於月、日和星期則不大清楚了。自從我住進這兒童院後,從來沒有親人(包括父親)來探望過我。
一九四三年的某月某日,大哥突然來探望我,給我帶來父親逝世的噩耗。他只簡單直接地說父親已經死了,也不說死因、怎樣死的和死在哪裡。奇怪,我聽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也沒有甚麼反應,心裡只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卻沒有流淚。
父親身體一向都很壯健,從未見他有病的,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死於營養不足,換句話說,就是餓死的。
父親既然不在了,整個家馬上不成家了,兄弟姊妹各奔前程,各散東西。戰爭的後遺症往往是「人亡家散」。
- 兒童院遷往貧民住宅
某年春天(正確年份記不清楚了),兒童院裡忽然傳出一個消息:說不久修女們就要離開我們,兒童院要解散了。一天,大家吃完晚飯,還未念飯後經,院長修女便走進飯堂來,搖起鈴,叫大家肅靜,用她半鹹不淡的廣州話,嚴肅地對我們說:
「各位小朋友,雖然修女們要離開你們,但兒童院不會解散,仍然會繼續,不久,你們會遷往一處比這裡環境更好、面積更大的地方,在那裡也有修女來照顧你們,你們放心吧!」
果然,過不了幾天,修女就叫我們全體大約九十個兒童收拾細軟,遷徒到距離筷子箕兒童院不遠的「貧民住宅」,葡文是:「Casa es Populi」,是由政府開辦的。在蓮峰球場(從前的跑狗場)的背後。正如院長修女說的,那裡果然是環境更幽美,地方更寬敞。長長的宿舍,排放在正門兩旁;宿舍前是個廣場,植有樹木,還有一口四季常清的水井,我們飲用、洗面、洗澡、洗衣等,都是用這口井的水。負責照顧我們的是四位寶血會修女,都是中國人,還有一位女教師;更有多位女工替我們煮飯、洗衣和清潔地方。
這貧民住宅,是由政府開辦的,一切經費都由政府負責,政府更派了兩位四粒星警長,輪值長駐院內。修女們若有甚麼問題解決不來時,也可以請他們來協助。
- 領洗皈依
負責照顧我們的四位寶血會修女,都很年青,活力充沛,熱誠能幹,尤其是院長陳修女,她甚麼也親力親為,為人和善,平易近人,我們都很喜歡她。這期間,她開設了慕道班,選擇了一些她認為有條件的、品學兼優的孩子入讀。班上人數不多,只有十多人(我是其中一個),由陳修女親自執教,為我們傳授天主教的道理。由於她教導有方,我們都很用心去學。大約過了一年左右,我們八位慕道者通過了當時花地瑪堂本堂神父的考核,獲准領洗。那位神父姓望,是一位廣東話說得不錯的外籍傳教士。為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我們八位慕道者,便在望神父的手,領受了聖洗。修女邀請了駐院的葡籍警長做我的代父,他的名字是Manuel Maria de Assuncao,那時我既不知道領洗要找代父,也不知道要取洗名,於是便矇查查地取了代父的洗名,Manuel。大約二十年後,我才知道原來葡文Manuel,即Emmanuele或Emanuele,中文是厄瑪奴爾;據《羅馬殉道錄》記載,我的洗名Emanuele是一位西班牙的殉道聖人,三月廿六日是他的瞻禮。
同年十月十三日,花地瑪堂慶祝堂慶,雖然花地瑪聖母瞻禮原本是在五月十三日。當天澳門主教羅若望來為花地瑪堂未領堅振的教友放堅振,我就在那天領了堅振聖事,取名為若瑟。
- 初次登台演劇
在修女的領導下,我們的團體,每年也有慶祝一些宗教節日,如耶穌聖誕、耶穌復活等,還有那時是國民黨時代,澳門每年的雙十節為國慶日,所有學校都隆重慶祝,日間有各樣的慶祝節目,晚上還有提燈巡遊。
我們的何老師是香港寶血會香港德貞女中的高才生(後來她當了方濟傳教會的修女),因受寶血會修女的青睞,畢業後獲聘來澳門執教。為了隆重慶祝雙十節,她編了一齣小型的歌劇,劇情非常簡單,內容是描述一個家庭,在抗日戰爭時,長兄從軍去了,家庭失散了,妹妹千里迢迢,去尋找長兄,終於找著了,大團圓結局。而我被選中飾演妹妹的角色,雖然我是第一次演戲,但由於何老師的悉心教導,也演得頗為出色,以致台下觀眾,連我的代父及修女們也熱淚滿眶呢!可能是劇情內容觸動了觀眾感懷身世,因而有這樣的反應吧!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結果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了長達八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香港也結束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當天下午約三時左右,我忽然聽見爆竹喧天,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故。因為當時我們既無報紙也無收音機,對外間的消息一無所知。後來修女告訴我們說:「日本無條件投降了,世界大戰結束了,世界和平了,我們到聖堂去感謝天主吧!」於是我們大夥兒,在修女的帶領下,進入聖堂祈禱,感謝天主賞賜世界和平!
- 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
世界和平了,大家心情也很輕鬆。當年花地瑪聖堂的本堂主任何心源神父,亦是我們的本堂神父和神師。他請修女揀選一些品學兼優的孩子,介紹到無原罪學校去讀書,修女於是揀選了六個新領洗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一位。當年九月一日,我們一行六個天真活潑的小伙子,穿著新校服,攜帶著新書包,開開心心地上學去。我們都是讀小學五年班。早上七時由貧民住宅出發,步行半小時便到達學校,午飯在學校吃,下午三時半放學,留在學校玩半小時,便回貧民住宅。當時無原罪學校的校長是陳基慈神父,他知道我們是貧民住宅來的,便特別關照我們。